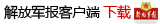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八连随之进驻上海南京路,担负警卫和巡逻任务。哨兵在霓虹灯闪烁的南京路上站岗,眼前是“大上海”的繁华热闹,背后是营门里的辛苦单调,加之国民党反动残余不断采取“腐蚀拉拢加破坏暗杀”策略进行抵抗,南京路,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一代代八连的战士面对考验,保持住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造就了声誉全军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在驻香港部队成立之初,人们称之为“新时期霓虹灯下的哨兵”——在繁华的自由之都香港,我们的战士面临着比八连战士更严峻的考验。
进驻香港以来,驻香港部队官兵遇到过多次向军车投掷反动刊物、不明身份人员要求建立联系、新闻媒体高薪聘请当“特约记者”和女色挑逗引诱等情况。
这样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拷问着驻香港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我们该如何教育官兵?
一、摇篮教育的不断尝试
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教导团被誉为“驻港精兵的摇篮”,选入驻香港部队的新兵、专业学兵和预提指挥士官包括轮换选调进来的军官干部都在这里培训。
尽管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教导团依然秉持大教育观,把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氛围建设相结合,并且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
地处创新氛围浓厚的深圳,教导团的团史馆建设得科技感很强。入口是“声光电”展示整体建设的电子沙盘,出口是集自拍、留言一体的互动设备;
教导团和深圳市图书馆共建,定期更新团图书馆的书目,补充当下的畅销书目。连队、食堂也都设有流动图书角;他们还准备了百部科教片,定期播放,开拓官兵视野。
教导团还有音效设备超赞的KTV,当下最新流行的歌曲都能点播;
网速流畅的红色网吧,电影、游戏、热门网站一应俱全。为了满足官兵的需求还建了“二期”工程,增设了好几十台设备;为了方便战士用摄像头,防止暴露军人身份,团里还专门开设换衣间……
这些都是针对“90”后官兵年轻化、精神诉求多样的新特点搞起来的。然而曾经的新特点已成历史,在当时先进、人性化的建设也显得落后了。曾经爆满的红色网吧随着智能手机的开放逐渐没落了。
我们该如何教育官兵这个时代拷问答案随着时代变化有了新的要义。
二、《大“话”教导团》问世
“要做这样的一个片子出来。”时任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教导团政委的刘佐鹏看到淮秀帮的创意配音作品,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这样的方法搞教育行不行?
于是他点将几名排长,制作一部讲部队故事的配音秀作品——《大“话”教导团》。
“可以做点有意义又好玩的东西出来了。”这是崔健、杨胜贤等主创人员受领任务后的第一反应。
的确,这也是刘佐鹏的初衷:做一个片子,寓教于乐,寓庄于谐,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教育官兵。
为了做好这部片子,主创团队在战士中收集当下流行的网络热词,发动全团官兵报名参与配音。3个月后《大“话”教导团1》首映,全团官兵的掌声和叫好让他们舒了口气。后来视频还在整个驻香港部队“巡播”,不少兄弟单位到教导团取经。驻香港部队政委岳世鑫看后也批示“好做法,要坚持下去。”
继第一部“大话”日常行为规范后,《大“话”教导团2》又聚焦“一日生活制度”,把枯燥的条条框框说得形象生动。现在《大“话”教导团3》正在筹备中,主题定为“智能手机的管理和使用”。
视频的文稿已改了三遍有余,除了纠结到底如何管理使用智能手机外,《大“话”教导团3》的主创,一群“新晋排长”也在思考:
配音秀out了,这次我们该如何教育官兵呢?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实践者并没有坐以待毙地等待谁给他们标准答案,而是在不断尝试中寻找正解。
三、在焦虑中赶路
《大“话”教导团》带来了多少正能量我们无从统计,但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能量并不只来自于结果,还有努力的过程。
对于杨胜贤、江宏这几个新排长来说,做这个片子不仅学会了视频制作的技能,其中桥段也成了讲教育课时信手拈来的案例;刘佐鹏在一开始就对主创团队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只要对传播教育效果好,就大胆去用去尝试。这种鼓励让这些未来可能走上政工岗位的人明白,教育要唯实不唯虚。
然而明白了教育“向”谁的问题,没多久他们又迷茫了。大“话”系列纵然有好的效果,但是工期太长了。而且一部片子不能代替日常的教育课。这样成功的尝试并不能回答“我们该怎样给官兵上课”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好的教育课要大道理+小道理,一堂课里二者的比例怎么调和?”
“传统教育课,到底怎样才算得到了好的教育效果?”
“深感个人能力不足怎么办?”
“都说百年树人,军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教育该如何适应这个现实?”
知易行难,教育创新的实践者往往比理论家面临更多的困扰。这种焦虑,基层政工干部可能深有体会。
时代抛出的问题有时候下一个时代的人才能看见清晰的答案。任何事业的开拓者都是在迷茫、焦虑中摸索着前进的。
正是这种“害怕落后于时代”的焦虑让他们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