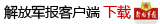创作要含古纳新。宋代赵构《翰墨志》语“前人作字焕然可观者,以师古而无俗韵,其不学臆断,悉扫去之”;唐代孙过庭《书谱》语“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两位前贤所语,道出了书法只有拟古方不落入俗套的真谛。拟古不是简单的复古,创新是要有独立书法语言的。临摹古代碑帖是从事书艺术的不二法门,也是提升书艺境界的重要途径,但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要从古代碑帖中走出来,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近几年,我参加了几次全国全军书法大赛评审,从参赛的情况看,不乏有走极端者,把古人之事做得极致,走进去而没有走出来;也有横向(当代人)取法者,把自我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古人则抛在脑后;也有古为今用,古今并用,融会贯通的。我觉得后者是智者。一幅好的作品,除品其章法、墨法、字法和笔法外,古法不可忽略,这是作品能否立住的“根”。在品评作品时,有时会听到“作品看起来比较新”的评价,这个“新”并不是创新之新,而是指作品缺少古法。
如何得古法?我在前面讲过要经常临摹古代碑帖,通过与古人对话从中获得前人的笔法、墨法和字法,有古法的作品才有厚度、有韵致。在此基础上,融入作者的技法和情感,由此而创作出的作品才有温度,才会成为经典。去年,中国书协举办了第二届书法临帖作品展,要求每位作者提供一件临作和一件按临摹范本风格进行创作的作品,这一敬畏经典和重视传统的有益举措,开辟了书法大赛的新河,我觉得此举意义在于既锤炼了书者的传统功力,也考验了书者的临创能力,这是一条融古铸今提升创作能力的绝佳路径。
创作要取法乎上。《易经》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此语可谓中国传统文化之智慧,只有立意高远,见贤思齐,才会有新意,才能有建树。如果平庸定位,只会“不有佳咏”,书法创作也是如此。
一方面取法要高古。米芾有“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光尤可憎恶也”,其中“高古”之意即为取法魏晋,觅之韵味,追之格调,虽然米元章讲得有些武断,但也表明一个时代代表性书家对追古的鲜明态度;也有人如此形容高古:“是时间漫漶在残碑断碣上的石花,是书蠹在吴笺蜀素上蛀出的虫孔,是魏晋诗人阔大衣袖里飘来的遗音”,此处高古之意展现的是颇具画面感的一道历史印迹。唐以前书法五体已经基本形成,中国书法体系基本完备,其后各个朝代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与延伸,因此创作时往“古”里追,其创作的作品则更显传统,愈加古味充盈。即使作品达不到理想的高度,求其次也是可观的。我并没有否认唐以后书法之意,历代书法都有经典,都有可学之处,上述的出发点主要是从中国书法史意义的角度来强调创作需要高古气息。
另一方面创意要高妙。也就是构思要新颖,尽量做到与众不同,甚至出人意料,让观者耳目一新。每次创作都有其初衷,每个展览都有其特定要求,尤其是主题性展览,把书写内容定准,再把形式与内容高度融合,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美术创作初期画家会设计样稿,参加重要书法展览是否也可效仿此举?书家对创作样稿可进行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当然,创作永远是以自然朴实为最高境界。苏轼曾语“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既是东坡居士直指艺术灵性的阐发,更是道出了创作立意的高妙之理
(2018年3月23日《中国文艺报》题目——《人生就像时钟,到子夜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