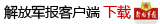书法创作有别于“写字”,它不仅仅是一项技巧,更是一门古老、质朴而又博大精深的艺术,是我们的国粹。它能以其高雅、深邃的审美内涵使无数人为之倾心。但它同我国其它艺术门类的创作一样离不开继承传统与创立新意。王夫之的“道日新”观点即认为没有千古不变的道,“道因时而万殊”。齐白石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也精辟地概括了继往与开来的哲理。在现代改革开放、各种文化相互交叉渗透的大背景下,书法艺术必将突破原有的樊篱,创造出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总趋势。如果没有创新,只是一味地继承过去,也可以称之为原样照搬,依葫芦画瓢,长此以往囿于古人之“怪圈”中不能自拔或不愿自拔,满足现状,则永远只能做“书奴”、“写字匠”,充其量不过是一台“复印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照相业、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各种各样几可乱真的复制品都能“克隆”出来。显然,纯粹的临摹和照抄已没有出路。难怪乎前人有言:“有李斯而古籀亡,有中郎而古隶亡”,意即死守古法必然步入死胡同,看来不无道理。我们既然要从事艺术创作,或多或少总要有些创的成份,即“变”如果都不思变,事业就不会再有友展,历史也将会停滞不前。针对具体的书法创作而言,除集各家之长于已外,还要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有意识地对笔法、字法、章法及墨法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追求一种或狂放、或飘逸、或稚拙、或清劲、或险绝、或凝重的艺术效果,进而表现出一定的个性特点,这本身就意味着求变。可以这么说,哪里有创新,哪里就有变化,“变”是创作的必然手段和根本规律。
由此可见,创作离不开变。否则就不成其为创作。其实,变也自始至终伴随着创作。这里我们权且将书法艺术创作分为继承与创新两个过程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其一,继承过程。依前所述,书法创作首先要继承传统,没有传统创新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继承传统的过程又可分为感知临习两个阶段。我们知道正确的学习方法都要从观察、研究优秀碑帖入手,在此过程中,即在感知阶段中,每个字的形象通过感官映入大脑并接受审视,但这种审视终究是有时间限度的。一旦这些形象脱离了人的感官的直接观照,其印象便立即以记忆的方式贮存下来。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就在感官脱离具体形象的那一瞬间,该物象在人的大脑中原有的形象立即开始泛化,部分地失去原有的丰富性、鲜明性和准确性。虽然我们常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类似这样的描述:“当时的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见”,但这种“清晰”是相对而言的。不妨我们还可做个试验,假使你所认识的人,哪怕是你最熟悉的人,当你们相处异地然后你再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其形象的时候,总是带有一种近似朦胧的色彩。也就是说当人的感官脱离了碑帖这一具体对象之后,留在脑海里的每个字的微妙变化不再象呈现在眼前那样明朗。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形象的某些部分,一般是引人注目、特点明显或使人感兴趣的部分可能被强化了,突出了,其它部分则可能被淡化了,甚至彻底消失了。可见,被感受的对象尚在脑海里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些程度上的变化。当进入临习阶段后,人自身的生理条件限制、书者的书写习惯、眼和手的配合能力、工具和材料的综合应用以及原碑帖本身所存在的模糊性等诸多因素都将构成临作与原作之间新的误差。这使我想起了曾经在一份刊物上看到的一篇吹捧一位当代书法“大师”的文章。捧者为了证明“大师”技艺的绝妙,竟声称“大师”能信笔写成两件以上包括尺幅、用笔、结构、用墨、章法甚至连飞白都绝对一样、精确无误的书法作品,并不知羞耻地配发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将同一件草书复印出两件然后一同发表的作品。其实他不过是利用了个别刊物编辑的无知愚弄三岁顽童而已。事实上,人体自身所具备的各种能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使是复印机、印刷机等还会受炭粉、油墨及纸张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微妙的变化。
其二,创新过程。这里我们再把它划分为审美与表现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在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中,人的审美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的审美为每个人的气质、修养、习性、信仰所决定,同时为时瓦气息所影响,是一种主观性、变动性比较强的心理活动。对同一审美对象,由于审美者的个体差异,因而产生的效应也不一样。有人喜欢雄强豪放的,有人喜欢稚拙憨厚的,有人喜欢雅致清秀的,有人则喜欢险绝奇恣的……,所以不同书者在创作过程中都将或多或少地融进自己的审美成份,使原来的造型带有个人倾向性的变化。以弘一法师为例。在他出家之后,由于受佛学之影响,其书风亦随之而变,字字尤如高士君子,平淡、清远之极,给人以静和之美。王铎的“奇怪论”也在其作品中得以充分表现。当代许多书家更是敢于打破古人常规,以时代的审美趋向为指南,全方位地借鉴、吸收、融合那些旧有的、但却被掩埋在瓦砾土堆之间长久为人们所遗忘的然而又极有价值的美的格式,如甲骨文、古陶、简牍、诏版、权量、封泥、墓志等,这些都成了他们调墨寄情的对象。他们还广泛接受各种信息,在多层面上不断提高、调整、扩展审美价值和容量。他们不但以雄强为美,还以新奇为美,使书法创作发展到了又一新的阶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事实上,每个时代都通过自己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发出特有的声音,反映那个时代特有的面貌,表现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趣。书法艺术虽然不能最直接地展示这些因素,但时代的审美趋势对作品潜移默化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否认的。三十年前人们对着装的美的要求同现在相比即是最明显的例证。另外,师法自然也可偶得新的审美气象,迸发创变的灵感。据资料记载,毛泽东当年为《红旗》杂志题名时曾加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中来的”。林散之也论道:“以字为字本书奴,脱去町畦可论书。流水落花风送雨,天机透出即功夫”,均道出了妙悟自然及“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谛。可见在审美这一阶段里,书者均在自己审美趋向主导下求变、求新。之后,书法创作当进入到具体表现阶段了。此时,书者要把自我确定的创作思想、创作意图具体地表现出来,即在实施挥毫作书过程中,还会受到作品幅式、表现手段、工具材料、创作心境乃至文字内容的影响和制约,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有一些是作者在自己的审美支配下所做出的有意的加工改造,有一些则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凭借直感、灵感等在不自觉和无意识的情况下,甚至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突发完成的。就最为基本的工具材料面言,笔、墨、纸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名目繁多、品种各异的毛笔不断上市,使毛笔的性能得以充分的施展。各种或传统、或现代的纸的生产,也使纸的质地向多元化发展。比如渗化的宣纸加上书者不同力量的倾注,不同水份的运用,均为线条疾、徐、枯、润、轻、重、粗、细的瞬间变化提供了灵敏度极高的场所。同时各个书家在使用工具时也有不同的习趣,比如不少人就敢于打破千百年来“中锋至上”笔法,大胆使用偏锋、散锋、逆锋,用墨也敢于突破禁区,不避涨墨,不弃枯笔,使墨韵美升华到了一种极致。这些创作都自觉不自觉地增加了出新的成份。再就创作心境而言,最佳的心境能使书者在创作时恍惚走入另一个世界,从心头到笔端好象有一股绵绵不断的“气”,一股近似神奇的“灵气”,这时所创造出来的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连作者本人也难以重复追求。孙过庭在《书谱》中也谈到了心境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这五种合益的情况下便可创作出良好的作品。五合之中除“纸墨相发”之外均与心境有直接关系。他指出:“合则流媚,乖则凋疏”,可见心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优劣。不管优也罢,劣也罢,总会给作品带来两极变化。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不变是相对的,变才是绝对的,是必然的。纵观历代书法大家,哪个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变出来的。唐代大书家张旭不为魏晋、初唐循规蹈矩之书风所拘敛,勇拓新面,大胆地创造出了势态奇异的狂草。其再传弟子怀素亦不被宗师的巨大成就所震慑,再创狂草连绵新姿。“杨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强烈反对当时书坛之柔靡书风,其所作漆书一变中国书法传统法度,从而达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创作境地。隶书大家伊秉绶熔秦篆、汉隶、唐楷与一炉,抛弃东汉晚期隶书的蚕头雁尾,创立了极具装饰效果且高古博大的新体隶书,被康有为誉为“分书之大成者”。另外象颜真卿、黄庭坚、米芾、吴昌硕、张瑞图、王铎等,他们无不以成功的创变,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假若我们的先辈们都泥于古法,死守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试想会有今天如此绚丽多彩的书法艺术吗?我敢断言,如果没有“变”,就没有书法艺术的今天,更不会有辉煌的明天。然而,并不是一切变形都可以进入到书法艺术的创作领域,更不是变得越离奇、越古怪、越丑陋就越好。时下一些书者不甚重视基本功的锤炼,而是生硬变形,过分夸张,刻意出“新”,急于求成。岂不知,求变还要遵循一系列美的规律,同时还要适当考虑我国的国情和民情,纯粹的脱离群众并非是最高明的创举。
无论任何人都要以发扬光大祖国的优秀文化艺术为已任,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来以对待艺术创作中的求变问题。尤其对于书法创作者来说,更要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要对祖国和人民负责,要在认真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力争创造出既具时代气息又不同凡响的唯我独有的书法艺术语言。切不可违背美的规律,只求时髦,不讲内涵,信手涂鸦,离奇怪诞。切记,真理迈过一步就可能成为谬误。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科技在飞跃,其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与时俱进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书法艺术亦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其变化能否为历史所接受,时间会做出最后的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