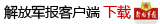张继篆刻:若行若藏
变法阶段,首先是对古法的灵活运用。清代印学理论大家周亮工曾有“取古人法而能运己意者可也”之精辟言论,清代另一位印学理论大家魏锡曾也有“推崇入古出新,讲求天真自然,反对墨守不化,摒弃矫揉造作”之学术立场,均影响深远。这是因为篆刻艺术虽然以实用的印章为起点,但在后来代代印人或可称之为篆刻家的不懈努力下,其生命力趋于愈来愈旺盛之势。可以说在其实用价值不断退隐的前提下能有如此之状,主要缘于篆刻艺术自身具有抽象表现审美意识的功能,具有弘扬艺术家主体精神、思想理念的能力特征,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它的无限趣尚。其线条本身的质感,线条运动所隐含的力与韵,空间构成所营造的势与气,边框运用所产生的视觉凝聚,无边处理给观者带来的张力,残破技法所表现出的朦胧意识乃至不同布篆法所生成的变化之妙等诸多形式美的元素都不可能简单地以外在形式所涵盖,只有注入作者的性情与学养方可悟得与表现。故而,在学习传统古法时不可盲目地“依葫芦画瓢”,须“心领”继而“神会”。正如书法学习中,临古有“实临”与“意临”之别,实临得其形,意临得其神,二者相得益彰,形神兼备矣。前代篆刻大家无不是灵活运用古法之楷模,如清黄牧甫即是在大量继承汉印平正方直,端庄博大的基础上灵活变通,使得“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于线条、块面、空间的组合分布与构成上极具形式美感,为后人所景仰。
其次是对古法的时代顺随。“艺术当随时代”,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篆刻艺术当然不会例外。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篆刻由实用走向纯艺术,由书画的附庸走向独立,由应用中的综合观赏走向展厅中的个性凸显,无不昭示着时代的特记。当今的时代是审美取向多元化的时代,反映在篆刻上,从文字的取舍、结字的多变、布局的设置、刀法的运用、边框的处理、款字的书刻以及钤盖的技巧均展示出古旧而又新颖的姿态,亦可称之为进行着一场艺术形式上的革命。就文字选择而言,当代篆刻很明显的一种现象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奇点,即不拘于甲骨、大篆、小篆或摹印篆的范畴,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文字发展过程中不甚成熟的过渡性书体,从中挖掘新颖的要素以求独到。大量非篆书、符号化、杂交体等带有浓厚时代气息同时又兼具历史厚度的新的体式每每使人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对于篆法,当代篆刻不斤斤计较于一字之美,而更注重整体布局,使字法服从于章法。把印文的可识性摆到了服从于艺术审美性的地位,故时时新意叠出。此外还有边框,这一对形式表现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元素亦被当代印人开发利用得淋漓尽致。在前人所有边框形式的基础上或使之厚重,或使之轻盈,或使之虚化,或使之工细,或使之写意,抑或去除边框,均为形式所用,实为其艺术内涵所用,但尽展时代之消息。当代篆刻一如当代书法,有人称之为尚“趣”,有人称之为尚“式”,也有人称之为尚“艺”,总之,是以广涉博取为胸怀,以崇尚个性为要旨。当代篆刻已不象明清从文人的角度去师法秦汉,而是更多地站在艺术的立场去弘扬秦汉精神。若一味照搬秦汉旧式或机械摹仿流派印形貌,少有时代气息体现者已很难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