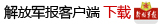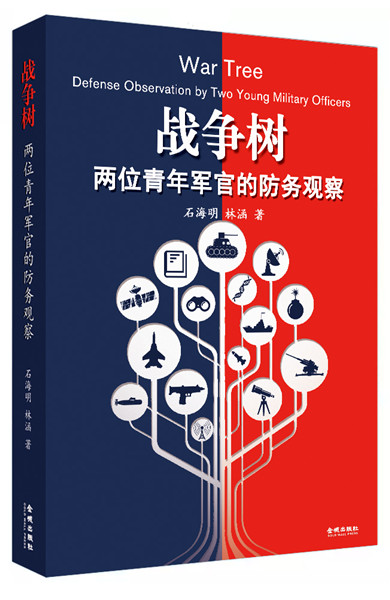
战争之树常青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最激烈、最残酷、最普遍的现象,由于事关利益集团的生死存亡,从一开始,就与科技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作战手段的急剧更新,催化着作战思想的激烈绽放,影响着作战体制的深刻变革,引导着作战模式的火速演进。如今,兵器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左右着现代战争的每一根神经。显然,在这种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并深刻影响军事领域的时代,一支军队对科技前沿的认知,已然成为一切军事活动的逻辑起点。
幸运的是,我们两位作者都先后在湖南求学,并于科技味道浓郁的国防科技大学获得科技哲学硕士学位,在那里遇到了朱亚宗教授、刘戟锋教授、曾华锋教授等几位恩师。从他们身上,我们感悟到了仰望浩瀚星空的情怀、从事理论研究的方法及走好军旅人生的自信。
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我们一直在合作跟踪研究战争理论问题。正如英国科技作家马特·里德利在《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中所言,“演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它是理解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变化的最佳途径。人类制度、人工制品和习惯的改变,都是渐进的、必然的、不可抵挡的。”“演变不仅仅局限于遗传系统,还能解释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改变方式:从道德到技术,从金钱到宗教。”大约在三年前,我们开始萌萌意识到要从演化的角度思考战争问题、军事问题及战略问题,从而构建一个不断生长的知识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牵引下,我们想到了本部作品的名字《战争树——两位青年军官的防务观察》。
我们认为,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飞速发展,战争形态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信息化战争方兴未艾,智能化战争、生物化战争又扑面而来。在此背景下,如何透视战争?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一是要深入理解战争的阶级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这也就是说,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并受政治支配的,而政治总是阶级的政治,是一定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深刻分析了战争的阶级利益和经济根源,明确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军事斗争实践,特别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打着人权的幌子发动的对外军事干涉,其实质还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当前,在关于战争带不带政治性的问题上,有人认为战争主体超越了阶级、政党、民族、国家,战争已不具备政治性。也有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命题只适用于过去,用政治的观点考察当代战争已难以区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其实,无论是高技术战争,抑或当代反恐战争,当代战争的主体依然是阶级、政党、民族或国家,战争主体没有改变,因而战争的政治属性也没有改变。
二是深切把握战争暴力性的新表现。战争的暴力特征,是战争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观点之一。战争的暴力表现为敌对力量的对抗,敌我双方战争体系涵盖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其构成要素也必然成为战争的目标。因此,战争不单是武力冲突,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斗争。依靠军事作战实现其政治目的,在军事上,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摧毁敌方支持战争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表现为尽可能地摧毁敌对国家的政治体系,进而将己方的政治意志强加给敌方;等等。
在当代战争条件下,单纯的军事作战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不能完全实现其政治目的。今天的战争所表现出的暴力性,已演变为一种结构性暴力。它包括在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的直接军事作战,更包括在认知空间、社会空间展开的“没有硝烟的较量”。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文化渗透、经济侵略等活动,就是这种结构性暴力的体现。尤其是在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前沿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强调网上意识形态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切实掌控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始终把打赢网上舆论斗争作为重要任务,赢得未来战争的制脑权。
三是深刻认识战争艺术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人说,战争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战争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战争具有确定性,人们可以借助“拓扑学”“博弈论”“模糊数学”“灰色理论”“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数理工具,让当代科学的光芒逐渐照亮战争的每一个角落,不断揭示出战争谋略的科学本质、思维规律、内在结构和行为方式,不断廓清战争的迷雾。战争之所以是艺术,是因为战争又具有不确定性,战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源自作战双方力量的复杂变化,另一方面产生于军事指挥员对形成、提升和运用战争力量的主观创造,而这种主观创造见诸军事实践,便是战争艺术。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人类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天地”。正是战争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为历代军事家演绎战争艺术提供了广阔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