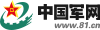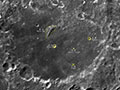两年前开始的那场“脖子以下”改革中,许多部队都经历了转隶移防。部队在新驻地驻扎下来,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但官兵要在新的营盘扎下根来,则像移栽的树木一样,也需要一个过程。有人说,如果把千里移防比作一场迁徙的话,那么每名官兵及其家庭适应移防后新状态的过程,则是第二场“迁徙”。请关注今日《解放军报》的报道——

部队移防近两年,有的改变仍然在路上——
第二场“迁徙”
■王 迟 雷兆强 闻苏
部队移防已近两年,妻子和女儿第一次来到新驻地探亲,第77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程加彬欣喜不已,特意抽出空来带着妻女逛逛营区,让她们看看“新家”。
一家四口刚走过家属楼的拐角,5岁的女儿就有新发现。“看,几棵‘枯树’!”孩子指着一片小树林大声喊道。
那是7棵碗口粗的杉树,每一棵都被3根圆木牢牢支撑着。时近初夏,周围的树木都已郁郁葱葱,这7棵树的断枝上只“点缀”着些零星的绿叶,不仔细看,的确像已枯死。
“这些树移栽不久,不是死了,是还没扎好根呢……”程加彬忙不迭向孩子解释。这7棵树,对于他和全旅的官兵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2017年的那场“脖子以下”改革中,程加彬所在的单位挥师南下,机动1000多公里,与其他几支队伍合编组建了现在的旅队。
官兵们在新营区种下7棵杉树,在每一棵树的根下埋上从老营区带来的土壤,寓意跟小树一起在新驻地扎根成长。
为了让这些树尽快成活,官兵们精心呵护,找来圆木撑着、买来营养液“打点滴”、铲除树下杂草……可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低估了一棵树在移栽后生根发芽的难度。
树犹如此,普通一兵要从西北黄土地“扎根”到南方红土地又何尝不难。“军人的背后是国,军人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回想起近两年来的日子,程加彬感慨:“不仅是我要适应新的环境,我们一家人都要适应新的改变。”
某种意义上,移防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是一种工作生活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切换。
有人说,如果把千里移防比作一场迁徙的话,那么每名官兵及其家庭适应移防后新状态的过程,则是第二场“迁徙”。
第一场迁徙,一声令下,他们打起背包就走,一天一夜便跨越千里。
第二场“迁徙”,近两年来,他们依然在路上,直到时间把改变变成习惯,把习惯变成自然……

因为部队移防,四级军士长宋文春的妻子分娩时他不在身边,女儿一岁多才第一次见到爸爸。今年端午节前夕,妻子又带着女儿来新驻地探亲,宋文春想借此机会好好补偿妻子女儿。田浩龙摄
1
新房钥匙还没拿到手,一家人已各奔东西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滚烫的日子在很多官兵心里都打下了烙印。
旅政委蒲毅也不例外。当时,在某部任职的他突然接到了担任某旅政委的命令。这个旅是新组建的,接到命令时,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得马不停蹄赶到西北,去迎接素未谋面的几千名官兵。
越野车在广袤的黄土地上疾驰,车窗外,祁连山脉起伏绵延,蒲毅心中紧张而又充满期待:部属们都是什么样的?未来,大家将融合成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在蒲毅的目的地——某团营区,挺拔的行道树下,几个战士穿戴整齐,正在合影留念。移防的消息一个月前已经宣布,尽管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开拔、去哪里,但自从门口的哨兵不再是本单位的战士,很多人便隐约感到:也许,下一秒就要出发了。
家属院差不多要搬空了。按照要求,全团六七十个随军家属也要离队。一名四级军士长把家具“扔的扔,送的送”,然后请假把妻儿送回老家。
干部王华的女儿从一出生就跟着他在家属院里长大,随军的妻子是一名医生。为了给这个家“一个窝”,王华东拼西凑攒足一笔钱,在驻地市里买了一套房子。没想到,新房钥匙还没拿到手,一家人已各奔东西。
连长吕明生的妻子李萧寒是哭着离开家属院的。几个月前,她辞去工作来到部队与丈夫团聚,并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驻地又找了一份工作。可没过多久,移防的消息传来,从老家一路追到部队驻地的她只好又原路返回……
宣布移防命令的时刻终于到了。移防誓师动员大会召开时,列兵鱼文彦站在整齐的队列里,军姿挺拔。他突然想到了新兵下连前的那次列队,那时,也有一个未知的地方在等着他,此刻,曾经陌生的远方已被他视作“第二故乡”。
嘹亮的军歌在操场上响起,紧接着,政委蒲毅站上前台,带着官兵一起高喊战斗口号。蒲毅认真看了看这些陌生的部属,一个个坚定的眼神令他至今感动:“说走就走,眼里看不出一丝犹豫,多可爱的战士,多好的兵啊!”
就在这一天,几百公里外,几支合编队伍中距离最远的一支已经出发了。出发时,马路两侧,站满了送行的战友,送行队伍的后面是一群抱着小孩的家属。三级军士长汪利江的妻子也在其中,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刚出生不到一个月。
“那感觉,就像是妻子送丈夫上战场。”出发前,汪利江亲手将驾驶了18年的坦克封存入库。一个月后,营区将移交给新的部队,妻子和孩子也将离开。
上士杨程辉安心地踏上了征程。临行前,妻子专门发来短信告诉他:“你忙你的不用管我,家里都好着呢!”
直到移防结束几个月后,杨程辉才知道,远在老家的妻子那时候正愁得焦头烂额:婆婆突发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儿子才一岁多,她每天照顾一老一小,晚上哄完孩子睡觉,还要给婆婆做两个小时的康复按摩……
在准备登上火车的队伍中,军医张红艳手推一辆婴儿车十分显眼。孩子不到两岁,移防命令宣布时正发着高烧。移防纪律要求全体官兵必须统一行动。家人都不在身边,孩子交给谁照看?征得单位领导批准后,张红艳把心一横,带着咿呀学语的女儿,和几千名战友一起奔向了未知的远方。

火车站内,移防的列车即将开动,军医张红艳带着发烧的女儿和战友们一起奔向未知的远方。刘波摄
2
“你去哪我就去哪”,一句承诺饱含万千不易
新营区家属院里的阳光正好,身怀六甲的张怡然扶着肚子,想到院子里转转。再过不了多久,这支移防后的部队,将见证又一个军娃在新的驻地诞生。
张怡然的丈夫张友新是旅保卫科干事。两年前,新婚不久,丈夫就跟随部队来到这里。张怡然犹豫了大半年,最终还是辞掉工作,追随丈夫,离开了土生土长的老家。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和无数的军嫂一样,张怡然也曾这样对“不安定”的丈夫许下爱的承诺。然而,这句话真的要变为现实,她才发现其中的不易。潮湿闷热的气候、陌生的人际关系、听不懂的方言……刚走进部队驻地所在的那座小城,西北姑娘张怡然感觉“浑身都不自在”。
好在住在家属院的军嫂不止她一个人,家住对门的军嫂杨荣,成了她的榜样。
杨荣是最早一批住进来的家属之一。她记得,当时原单位留下的这座小院子里杂草丛生,“草比人都高”;家属房内瓷砖掉了,灯泡也没有。杨荣就带着两岁的女儿,如燕子垒窝,一点一滴搭建新家:换马桶、贴瓷砖、修洗衣机……
张怡然刚来队时,新家简陋得连床都没有。丈夫去外地驻训了,她就在地上铺个垫子,带着腹中的孩子睡下去。
聊起那段日子,军嫂们都开玩笑说自己是“女汉子”,甚至还要较出个高下。
女人堆中,张怡然激动地讲述自己的“事迹”,好像生怕说慢了,“荣誉”就会被人抢走。说这些的时候,她神情轻松,仿佛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正说着,家属院来了一辆越野车。张友新从外地扶贫回来了,第一时间便回家看看有孕在身的妻子。
在大家的起哄下,张怡然拿丈夫取乐:“你天天扶贫,你也来扶下我这个‘贫困户’呗!”
“我工资卡不就在你那里么!”张友新呵呵傻笑,心中却对妻子的牺牲付出一清二楚。为了一家人团聚,张怡然辞掉了之前在省城大银行的工作,如今在这个小县城的一家支行当临时工,每月基本工资只有一千多元。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句话里蕴藏的坚决、勇气、牺牲和无奈,每个移防后的军人家庭都有一份自己的注解。
前年,程加彬晋升为四级军士长,达到了家属随军条件。然而,申请家属随军的报告还没批下来,部队就移防了。以前的驻地属于艰苦边远地区,移防到新的驻地后,驻地环境改善,随军条件随之提高。这一新情况,程加彬过了好久才小心翼翼地告诉妻子——“等了那么久,等来的却是下一场等待,怕她伤心……”他说。
丈夫从家门口移防到千里之外,军嫂刘小雯看上去倒是波澜不惊。“远近都是我一个人,都一样。”结婚10年来,丈夫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她独自一人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早已习惯了为整个家庭遮风挡雨。
移防之际,士官李志亮的妻子李文婷突然被检查出癌症。为了不成为丈夫的拖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头发脱落、瘫痪在床的李文婷,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恢复训练。
从走路都困难,到完成3公里长跑,再到半程马拉松,这位军嫂奇迹般地重新站起来了。去年年底,在妻子的支持下,服役满12年的李志亮选择了留队继续服役。
今年春节前夕,旅里组织了一场感动全旅人物的颁奖晚会。评委会将唯一的集体奖,颁给了全体军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