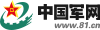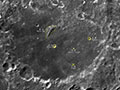3
改变自己是最困难的,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值得
“明年绝不留队!”两年前的那个夏天,移防到新的驻地后,已服役11年的刘健暗自定下了一个决心。
初来乍到,第一次武装5公里越野训练,刘健发现,自己还没开跑,身上的迷彩服就已经湿透了;奔跑的过程中,上顿吃下的“重口味”饭菜,让他感觉“胃里像是热辣辣的火锅在沸腾”。
刘健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里”。可是,过了不到一年,刘健当初的那个想法就动摇了。“适应就好了,其实一切都是自己的小情绪在作祟。”刘健反思道:如果一名军人连驻扎的环境都适应不了,怎么适应战场啊!
移防给官兵带来的挑战并不只是适应环境那么简单。移防伴随着转隶,也伴随着部队的重组转型。当曾经的摩托化步兵们融入“合成旅”这一全新的体制编制,一大批官兵都面临换岗转型。
对于四级军士长赵明来说,一门牵引式高炮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军旅生涯。移防后,赵明手中的武器从高炮变成新型防空导弹,10多年的火炮操作经验再无用武之地,“感觉像是被时代抛弃了”。
然而,没有人愿意就此放弃。
告别那辆老式的履带坦克,汪利江的“坐骑”换成了新型轮式装甲突击车。“主战装备从一代直接升级为三代半,而且当年接装当年就要拉上演训场,压力太大了!”当兵的第19个年头,汪利江仿佛又回到了新兵时的坦克训练基地。
爬车底、翻资料、学理论、请专家……一年多后,10万字的教材和简易明了的“汪氏口诀”,开始在全旅推广。
“改变自己是最困难的,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汪利江很清楚,适应改变的过程远比那条千里移防的路程更艰苦、更有挑战性。
对年轻的干部赵权来说,来到新单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被“编余”了。没有岗位、没有职务,赵权一度觉得前途迷惘,生活中“没有一点色彩”。
或许正是因为内心的焦虑和不甘,2017年底,参加集团军“四会”教练员比武时,赵权拼尽全力,一举夺冠。战友们的赞许扑面而来,赵权内心产生了一种久违的自豪感:“感觉还是有价值的。”
赵权顿时感觉天地为之一宽。后来,他当上了火力连指导员,带着这个全旅合编单位最多的连队,很快实现了“合心、合力、合拍”。
“三年不鸣,久久为功。”该旅组建之初,面对战备形势任务转变和部队建设转型,旅党委定下决心:要努力让每名官兵都在这场改革中完成全方位的转变,从而激发出旅队蓬勃发展的内生动力。
两年来,把几千名官兵从大西北带到大西南的蒲毅,亲眼见证了大家在“第二场迁徙”中的表现——
去年年终考核,这支移防仅一年多的部队,取得了全集团军总分第一的成绩,干部的考核成绩尤为亮眼。63名战士拿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其中生长军官数量占到了战区陆军部队的七分之一……
那些曾对南方夏天感到闷热难耐的官兵,已经习惯了汗流浃背地奔跑前行。
4
树还没有生根,我们已经扎下了根
南方盆地的雾气起了又散,散了又起,转眼间,就到了程加彬送妻女离队的日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刷新,发生在该旅营区内外的“第二场迁徙”始终脚步不停——
乘坐高铁,四级军士长韩晓强的妻子带着女儿又一次抵达新驻地。高铁开通后,与丈夫相见变得便捷,妻子已经逐渐喜欢上这个新家,女儿更是吵嚷着这次要再吃几顿罗汉笋。
“闺女能进市外国语学校了!”午饭过后,干部王华接完一通电话,连忙与妻子分享喜讯。妻子刚刚随军到部队不久,女儿入学的问题就解决了,令夫妻二人对未来的生活更加充满信心。
“整6斤,顺,坏小子,给你妈疼坏了!”儿子出生了,张友新兴奋地在微信朋友圈“广而告之”。这个小军娃的到来,既是小两口爱情结出的硕果,也意味着这个小家庭在南方小城扎下了根。
走出家属院,在该旅营区内,全新的训练设施已经建设到位,野外训练场和综合战术训练基地已经投入使用,参加上级比武的多个集训队正在紧张备战。
海拔4000多米的昆仑山腹地,旅里一批官兵正驾驶着新型装甲突击车在高寒山地检验训练成果,“一个月打了以前一年的弹药量”。
对于这些投身强军事业的新时代官兵来说,移防是个人和家庭面临的一场“随机导调”演练,也是通向胜战之路上的一个必经节点。
将妻子和女儿送到小城的车站后,程加彬赶在操课的号声响起之前匆匆回营。移防后,营区变了,军号声里的召唤和力量在他心中丝毫未变。
妻子探亲期间,看到他一次次在军号声响起时露出的紧张、兴奋,不禁感慨:“还是那个样儿,不管部队搬到哪儿,这些东西早都在你心里生了根!”
“生根!”看到营区里那7棵绿意点点的杉树,想起妻子的这番话,程加彬突然心生感触:“树还没有生根呢,我们已经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