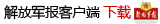出海
1985年11月20日,天气晴朗,青岛栲栳岛清风习习,海鸥嘶鸣。10点整,403艇松开最后一根缆绳,驶离码头,进入航道。
每天早上,五指-1岗位(机电长值更岗位)会拉响蜂鸣器,广播:“艇员起床!”照例传出常保林的声音:“同志们,早上好!今天是×月×日,出航第×天,封舱第×天,我们离完成任务90昼夜还有×天,我们在水下长征的征途上又迈出了一步!”
核潜艇水下航行时,不同舱室温差极大,温度最高的有35℃,温度最低的要穿棉工作服。二舱上层是潜艇的指挥中枢,二舱中层是生活舱。艇长室、政委室都设在二舱上层。
艇上实行严格的一日生活制度,程文兆分管行政管理。
33岁的机电长金国祥是艇上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长航推迟了婚期,也因为承受了辐射剂量推迟了要孩子。高温高辐射的反应堆舱出现故障时,他经常带头往里冲。

航海业务长任德宝观测航道障碍物。图/受访者提供
由于航行位置包括很远的公海海域,基地岸上指挥部(简称“岸指”)有时会直接向指挥组发出绝密电讯,下达任务。为了防止计划被泄露,岸指有一次还下令潜艇临时修改了航路。
出航后不久,海上刮起了八级大风,阵风九至十级。几千吨重的核潜艇在大海中像一叶扁舟漂摇。巨浪像子弹一样打在外壁和舷窗上,北风呼啸声、舰体震动声、反应堆轰鸣声交织。潜艇横摇20多度,上下起伏达数米。
绝大多数艇员都吐了,抱着脏物桶呕吐,甚至吐出黄水和血丝。休更人员躺在晃来晃去的床上无法入睡,有人甚至把自己绑在床上。核反应堆控制屏前的几个艇员一边紧盯着让人眼花缭乱的仪表盘,一边不时把呕吐物收进罐头盒里。
常保林和副政委李敏信一整夜不断到各舱室查看。政工干部极少有人晕船,常保林认为可能与职业有关,因为他们倒下就无法做人的思想工作了。
次日上午,潜艇潜入水下航行,变得非常平静,艇员们终于睡了个好觉。
出航第6天,海上临时党委召开会议,决定提前进行封舱试验。封舱试验,即潜艇下潜后,在与大气隔绝的情况下水下航行。
海军下达的任务是20昼夜。封舱前的动员大会上,孙建国和常保林表示,如果条件允许,争取突破,越长越好。
12月10日,出航21天、封舱16天后,潜艇顺利进入计划海域,试航进入第二阶段。
艇员开始出现疲劳,机械隐患也开始增多,反应堆运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浓度也在逐渐增加。
成千套机械运转产生的废气、艇体的油漆挥发、一百多人的呼吸和新陈代谢、做饭的油烟等,核潜艇内的有害气体有上百种,能定量监测出来的就多达80来种。长期与大气隔绝,舱室的有害气体越来越多。
20昼夜过后,杨玺召开会议,研究上浮时间。会上,有人认为既然海军下达的任务已完成,应结束试验,最后决定:争取完成29昼夜、30个天文日。
封舱第22天时,舱内的放射性尘埃剂量已超出正常大气几十倍。部分艇员开始出现血压不稳、心律不齐、视力下降、牙齿出血、疲倦乏力、失眠等不良反应,高噪音也使人烦躁不安。
第一个月精神心理压力最大,最为难熬。不见天日的水下生活会让人一觉醒来陷入茫然,迟钝麻木,分不清是早是晚,眼前没有24小时制天文钟的时候,就想想上一顿饭吃的什么来判断。
每天早上,人人都抢着去撕指挥舱的月份牌,渴望一天快点过去。副艇长蒋松才在日历上写了一句话:“你撕不如我撕,一天只能撕一张。”有人对了下联:“我快不如你快,一天还是一样快。”横批:“度日如年。”
“一旦超出了人体的生理极限,再坚定的立场和意志也扛不住。”航海业务长任德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快40岁的他代表基地机关参加长航,他要求自己保持积极良好的形象。即便如此,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铁罐里,他也会在某一刻突然脑子一片空白,甚至闪过恐惧。他觉得潜艇内外分明是两个世界,甚至开始疑惑,难道就这样了吗?蓝天绿树永远都看不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