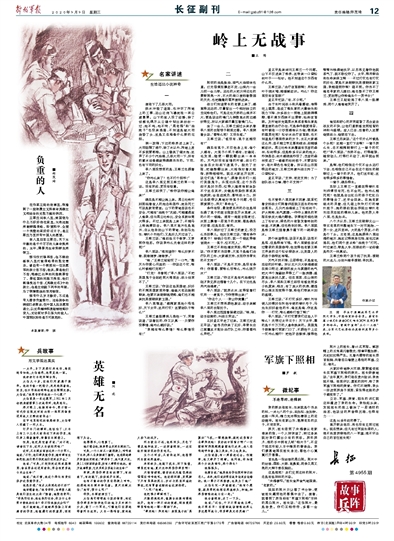一
接连下了几场大雨。
洪水冲毁了道路,也冲坏了阵地上的工事,远山近岗飞瀑流挂一派云遮雾罩。山下的敌人没了动静,除了侦察机偶尔从云缝中钻出来匆匆一过,炮不鸣,枪不响,“黑老鸹”和“油挑子”也没来捣蛋,不知道是被大雨浇昏了头,还是又在准备什么新的花招。
稍一放晴,下边的给养送上来了。大雨阻隔了通行,除了水以外,阵地上差不多就要断粮。山上修筑了储水池,还弄了不少个汽油桶,几场大雨一下,所有的蓄水设备都装得满满当当的。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
李八里没想到的是,王翠兰也跟着上来了。
“你咋么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这是李八里见到王翠兰的第一句话。没有欢迎,更没有惊喜。
王翠兰却笑了:“给你说你能让俺来?”
确实是不能让她上来。黑云吐岭时刻面临着敌人的炮击和轰炸,流血死亡可说是家常便饭。山下的营地虽说也不安全,可能有“油挑子”光顾,可能遭遇敌人偷袭,但与黑云吐岭比,安全系数毕竟大得多。不过上来就是上来了,不能马上给她撵回去。李八里不高兴也是高兴,自从他告别山下的营地,告别马先生、喇叭小刘他们,又是好几天过去了。
王翠兰说:“俺前些日子做梦,又梦到你挂彩。你说我咋么光做这样的梦呢?”
李八里说:“谁知道你?啥么好梦不做,就做瞎梦,瞎做梦。”
“唉,”王翠兰轻轻叹了一口气,“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你说这个仗,啥么时候能打完呢?”
“打完?早着呢!”李八里说,“不把美国鬼子全部赶到大海里去,战斗结束不了。”
王翠兰说:“你说这些美国佬,好好的不搁美国家里待着,偏偏大老远跑朝鲜来,他要不来朝鲜搞侵略,俺们也不能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李八里嗔道:“都搁家里抱小鸡怪好,天下太平,还用打仗?还要部队干啥么?”
王翠兰拿胳膊拐儿捣他一下,笑着说道:“说着玩的,你又认真……只要你没事情,俺咋么都好说。”
“我能有啥么事情?啥么事情没有!”
二
照明的油是柴油,烟气大油烟味也重。灯光昏黄而飘忽不定,山洞内一会儿明一会儿暗。远处的火把只将近处的景物照亮一片,不大的洞口接纳着微弱的天光,也把隆隆的雷声接纳进来。
战士们知道营长的老婆上来了,都离得远远的,尽量留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给他们。可是这处天然的山洞并不大,要是说话的嗓门儿稍微高点两边都听得见,所以大家都尽量压着嗓门儿。
坐了一会儿,王翠兰探过头来扒着李八里的衣服领子朝里边看。李八里侧着头说:“看啥么呢?又没生蛆。”
王翠兰说:“蛆没有,虱子还能没有?”
确实有虱子,不仅他身上有,每个人都有。大虱子小虮子都有,衣缝间、毛发里,随便一翻就翻出来一串串的。天气好没有敌情的时候,战士们会坐在太阳底下逮虱子。脱光了衣服,把缝隙翻出来,大拇指对着大拇指,挤得啪啪响。就这大家还开玩笑,说它们是“革命虫”,跟着同志们一起打美国鬼子。乐观归乐观,这个东西却不是好东西,咬得人瘙痒难耐坐卧不宁还在其次,关键是传染伤寒或其他疾病,会造成减员,影响战斗力。所以各级很认真地对待虱子问题,号召群策群力,消灭“革命虫”。
条件有限,最简便实用的办法是将生满了虱子的脏衣服放在开水里煮,大的小的一锅端。通常一堆脏衣服煮过,水面上飘着一层虱子的皮屑,看是确实不好看,但是实在、管用。
李八里听过了王翠兰的意见,没怎么当回事儿。他对王翠兰说:“哪有条件煮虱子?缺锅少灶的,就一个锅还得做饭烧水……虱子,咬不死人。”
王翠兰不和他嬉皮笑脸,很严肃地说:“你不要不当回事,灭虱子是俺们治疗队的工作,大家都支持,反而你当营长的不支持?”
李八里说:“不是不支持,是没有条件!你看看,要啥么没啥么,咋么烧开水?”
王翠兰说:“你这不是有汽油桶吗?刚才我见那边摆着十几个。在下边也是用汽油桶煮。”
李八里说:“就那点水,还得留着打仗用……煮虱子,亏你想得出来!”
“你这个人……我让你窝囊!”
王翠兰不想再跟他废话,动手来解李八里的衣服扣子。
李八里边扭捏着躲避边说:“唉,唉,动手动脚的,叫战士笑话。”
正好孟正平走了过来。王翠兰对孟正平说:“教导员你来了正好,李营长自己窝囊还不配合治疗队工作,你看看咋么弄吧。”
孟正平是来询问王翠兰一个问题。山下不仅送来了给养,还带来一口袋松树叶子——松针。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王翠兰说:“治疗夜盲眼啊!用松树叶子烧水喝,能缓解症状。咋么?你这里没有夜盲眼?”
孟正平忙说:“有,不少呢。”
由于长时间战斗和风餐露宿,难得吃上蔬菜,造成了维生素的大量缺失和视力下降,许多战士一到晚上就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辨不出景物,俗称夜盲眼。及时地补充蔬菜水果或者维生素是最直接的治疗办法,可是条件极度艰苦,有时候连一口炒面都难以为继,哪里来的蔬菜吃呢?松针水治疗夜盲眼,也不知道是打哪里传来的方子,反正大家都这么用,虽不能立竿见影和根治,却能缓解症状。黑云吐岭本来覆盖有茂密的森林,松树很多,但是给多日以来的炮火、炸弹轰击,树木都烧焦炸没了,茂密的森林变成了一截截的枯树桩子,不要说松针,连片绿色也难见着。所以在山后面很远的地方,王翠兰特意叫战士捋了一口袋松针。
孟正平说:“支持,肯定支持!为了部队战斗力嘛,哪个不支持?”
三
也不管李八里同意不同意,就紧忙着安排战士们照着师医院王医生的吩咐去落实。几只汽油桶架上了松枝树干,炉火熊熊,热气蒸腾,一件件土黄色的军服在铁皮大桶内翻卷。炊事班的锅也烧上了松针水,绿色的汁液散发着特别的味道,不刺鼻,但也绝非好闻。李八里就是给王翠兰捏着鼻子灌下的一碗绿汤水。
那个味道很怪,说苦不是苦,说涩不是涩,但是很难下咽。李八里曾经尝试过缴获的美国咖啡,他觉得他老婆王翠兰弄来的这个松针绿汤水,比美国人的药汤子咖啡还难喝。
天气不阴不晴,云层很低,不是敌机活动的好时候。所以五六只大铁桶都架在洞口附近,燃烧的炭火与蒸腾的热气把大半个掩蔽部弄得工厂一般沸腾,温度高出来好几度。但在里面,在山洞的尽头,李八里和王翠兰却没有感觉到多少热度来,相反,有了炭火的烘烤,潮湿的山洞反而变得干燥,给他们带来片刻的温暖。
王翠兰说:“不打仗多好,喇叭刘爷俩儿好模好生吹他爷俩的喇叭号子,马先生好好教他的书,俺还是俺,你还是你……打仗,啥么都给打毁了啊!”
李八里说:“不打仗要我们这些人干啥么?光想过太平日子!天下太平,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拿命换来的。美国鬼子眼瞅着打到家门口了,不跟他干上这一仗咋么能行?把他牙齿揍掉,揍得他嗷嗷叫唤满地找牙,以后再见着你他就客气了,就不敢咬你了。太平,得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啊……不过打仗也有打仗的好处,要是不来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能碰到你啊?碰不到。你当不了俺老李家的儿媳妇,俺也娶不了你王翠兰,更别想让你给俺生个一男半女!”
王翠兰又轻轻捣了李八里一胳膊拐,两个人偷偷地笑开了。
四
愉悦和舒心的欢笑驱散了思念逝去战友的不快,让他们重新感觉到短暂的祥和与温暖。故人已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活下去。
王翠兰后来说:“这个仗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还能一直打下去啊?一辈子那么长,总不能搁朝鲜打上一辈子的仗吧?”李八里说:“当然不会。打得越狠,越较劲儿,打得打不动了,和平就会到来。”
是啊,他们相信这个仗不会永远打下去,也相信自己不会在这个陌生的朝鲜过上一辈子的岁月。他们还年轻,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做。
一辈子,确实很长。
实际上王翠兰一直都觉得喇叭老刘师傅没有死,也不会死。他咋么能死呢?他就是去出红白的场子忙红白的事情去了,迟早会回来。在她老家皖北的灵璧,但凡碰上吹吹打打的喇叭班子,她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喇叭老刘活灵活现的模样儿来。他的男人李八里,也是如此。
八个月以后,王翠兰在朝鲜元山一带五老里的休整地生下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龙凤呈祥。大的是个男孩,小的是个丫头。五老里,这是她跟李八里结婚的地方,她还记得洞房花烛,敌机过来捣乱,他们两个差点给“油挑子”打死。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而眼前的一切却像是昨天一样真切。
王翠兰给两个孩子起了抗美、援朝的大名儿,分别叫做李援朝、李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