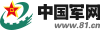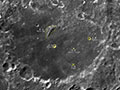洗过梨之后,一个战士说:“副连长,吃吧。”我说:“你们吃吧。”“还是你先吃吧。”“还是大家一起吃吧。”“那我们就吃了?”“吃吧。”“咔嚓”“咔嚓”“咔嚓”。三个“咔嚓”过后,我们都笑了起来。“真甜!”“是,真甜!”我想象,当时要是将那“咔嚓”的声音录下来放给人听,没准儿人家会误以为是进了蚕房,会以为是蚕宝宝在贪婪地啃食桑叶呢!其实,是馋嘴的副连长带着两个馋嘴的战士在吃梨。说出来你也许不会相信,20斤梨,我们没用半个小时,就吃了个干净。他们俩的那两兜梨我没让动,要是真的放开吃,我估计也得吃干净。还是我先站起来的,我说:“差不多了吧?”“嗯,差不多了。”“还能吃几个?”“起码还能吃三个。”“算了。”“算了。”“那就算了吧。”“走?”“走。”“回?”“回。”“那就回?”“那就回。”
我们就这样回了连队。不久,我被调到了兰州军区机关,永远离开了我可爱的连队。1989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值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狂轰滥炸”之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真的不知道写点什么才能进入流派,蓦然间想起了小姑娘手里的大金梨,便不由自主地写了一组诗歌,其中有一首诗叫《15斤梨》,就是根据这段经历写的。为了真实,我将20斤梨改成了15斤,全诗发表于1990年《星星》诗刊第2期,现抄录于后,以此作为我对遥远的军旅生活的纪念吧——
我曾在土沟的摸爬之中
强烈地思念过它
我的四肢
和我的胃 以及我的大肠
我的皓齿 都思念过它
我几乎是用我的所有的思想
思念过它的重量 多汁的
利齿的 偶尔咬到核儿
便有一股酸得两腮生津的敌人
袭击我的牙齿
在思念它的日子里
我想起过童年厌食一切水果的
那副讨厌的样子
想起过白色如雪的梨花
她站在梨花下
把鼻子伸到低垂的花蕊
我闻着嗡嗡嘤嘤的芬芳
并被偶然的走神儿
吓了一跳 梨
梨 梨
我在平静的营帐里 多次想起梨
想起它多汁甜蜜的脸庞
嘴不由自主地张了开来
也许是在梦里 一口一口地咬它
那滋味儿 那滋味儿
那滋味儿人生只有一次
并且在嚼的时候
还有咔嚓咔嚓的音乐伴奏……
是啊,那啃梨的声音是多么美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