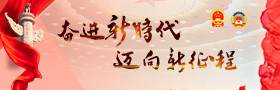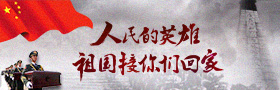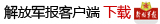越冰河,跨昆仑,戈壁大漠驰飞轮,拂晓5点马达响,夜半三更才宿营,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一名青藏高原汽车兵的日常。对他来说,回忆起那段日子,最怀念的就是纳赤台兵站的那碗烧豆腐。请关注今日出版的《解放军报》的详细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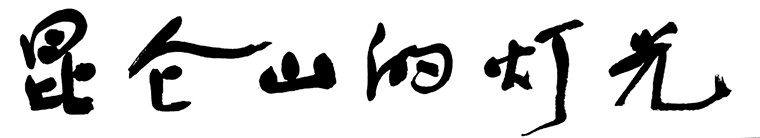
昆仑山的灯光
■窦孝鹏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是青藏高原的一名汽车兵,部队常年执行繁重的运输任务:越冰河,跨昆仑,戈壁大漠驰飞轮,拂晓5点马达响,夜半三更才宿营。茫茫青藏线上人烟稀少,陪伴我们的就是那些设在路旁的兵站。兵站一般100多公里一个,每晚我们都自带行李在兵站住宿、进餐、给汽车加油。兵站成为我们汽车兵的多半个家,一年中,我们住兵站的日子比住连队的日子多。时间一长,每个兵站的人员、甚至饭菜特点,我们都熟烂于心。如不冻泉兵站的葱爆兔子肉,当雄兵站的烧牛肉,黑河兵站的绿豆米饭等等,都在汽车兵中叫响了。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是被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授予“红旗兵站”称号的纳赤台兵站的烧豆腐。
处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常年云雾缭绕,每当夜幕降临,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便会被点亮,它成了我们心中的一种标志。多少次,奔波一天的汽车兵在薄暮中老远一看见那盏红灯笼发出的光亮,心中便会涌起一阵温暖和力量:啊,到家了!可以美美饱餐一顿,好好歇歇腿了。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开的车在半道上抛了锚,由于雪天路滑,只听“扑通”一声,车子掉进了路边的一个雪坑里。在战友的帮助下,车子被拖了上来。但有两片钢板被颠断了,水箱也颠得漏了水。副连长看了看,留下修理班长和我们车组一起修车,嘱我修好后赶到纳赤台兵站去会合,便带车队走了。
这里是可可西里无人区,我们冒着飞扬的大雪和刺骨的严寒修好车辆后,时间已到了晚上21时30分,我们几乎被冻僵了,几个人顾不得喘一口气,急忙打开车灯,开车上路。
终于,我们看见纳赤台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了。我一看表,已是凌晨零点40分。副驾驶员小乔嘀咕道:这么晚了,看样子我们吃不上晚饭了。
我笑了笑说:放心吧,炊事班的老班长是不会让咱们挨饿的。
果然,听见我们车子的响动,红灯笼下的餐厅棉门帘一掀,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兵站炊事班的老班长徐宏武。
徐班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餐厅,每人先送上一碗温开水。我歉意地说:“老班长,让你久等了!”他一瞪眼:“废话!你们最后一台车不到站,我能封炉关灶吗!”
原来,每晚不论多少车队住站,老班长都要找带队干部了解途中有无抛锚车辆,哪怕只有一台车未到站,他也要备好饭菜一直等着,这已是他的铁规。
不一会儿,一盆高压锅蒸的米饭和面条,一盘肉末烧豆腐、一盘肉丝炒豆芽便送上了餐桌。这地方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米饭面条都煮不熟。老班长嘟囔道:“我向你们连长打听了,你们3人中有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所以准备了米饭和面条,慢慢吃,别烫着。”
小乔眨眨眼说:“老班长,你的话太烫人了!”至此,我们身上的寒气和疲劳一扫而光,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徐班长是闻名青藏线的老模范,老高原都知道他是1951年入伍的陕北汉子,是跟着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进藏的老军人,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已离不开青藏线了,后来就索性转业到兵站当了炊事班长。
当时,由于气候原因,兵站沿线都不能种菜,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成了高价钱。
还有,上级发的许多黄豆,他只能靠着锅台边的热气给大家泡豆芽吃,他想做豆腐,给大家改善伙食,一方面缺乏工具和设备,另一方面技术上也不入门,这让他很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