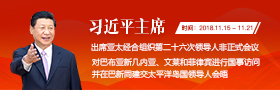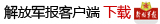潮涌边关,沧桑巨变。历史总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留下特殊的印记,以昭示和启迪人们,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科技创新发展,边防建设提速。放眼今日边关,我国边防建设已迈入高效立体管边控防新时代。
吾甫浪沟,全军唯一骑牦牛巡逻的边防线;墨脱,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建制县;古林钦山口,全军海拔最高边防巡逻点。在祖国漫长的边防线上,这3个地名,也许并不为人所知,但“唯一”“最后”“最高”等字眼,让人不禁联想到“缺氧、艰险、恶劣、严寒”,也让边防军人的牺牲和奉献,穿透岁月和时空的隧道。
北斗卫星指引巡逻,直升机空中巡航,护卫舰巡逻海疆,“蓝鲸”潜航碧波之下……今天,多样化执勤、立体化管控筑牢一道钢铁长城,守卫着各族人民的美好家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登高望远,我们发现,稳边固防离不开强大国力的支撑,戍边守防更离不开一代代戍边人的忠诚勇毅、责任担当。边海空防牢不可破、安如磐石,靠的是无数边防军人献身使命的精神传承。这是确保边境安宁的恒久力量源泉。
——编者
随着墨脱公路建成通车,边防官兵守防条件、执勤质量今非昔比——
进墨脱:从路在梦里到路在脚下
■严贵旺

现在,车队可以经常往墨脱边防运输物资。 马军 摄
边防官兵戍守墨脱,都是从跋涉山路开始的。
当年,墨脱不通公路,官兵只能在每年6月到9月—多雄拉山的开山期,徒步进驻墨脱。
1998年入伍的周国仁,是在次年夏天打着背包、拄着手杖,跟着老兵从林芝市米林县向墨脱进发的。
“进一次墨脱,就像经历一次战斗。”忆及当年,周国仁感慨颇多,“进驻墨脱,得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
百里进山路,也是一条“生死路”。官兵从米林县派镇出发,沿途翻越海拔4700多米的多雄拉雪山、天险“老虎嘴”,数次穿越千年不化的冰川、飞流直下的瀑布,通过蚂蟥肆虐的原始森林……

条件改善后,墨脱边防营某连也连上了水泥路,直通巡逻点位。马军 摄
“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西藏始末纪要》中,对墨脱边境地区有这样一段描述。
说是路,其实没有路,官兵在荆棘林中开路、在悬崖上架梯,在绝壁上攀岩、在江河上溜索,一路上险恶不断。巡逻一次,最短要3天,最长则需15天。
老营长文豪在墨脱守防11年,在近200公里的漫长边防线上,他先后31次走掉脚趾甲。墨脱边防营先后有近30名官兵献出宝贵生命,其中多数倒在了巡逻途中。
周国仁打小在昆明长大,经常听老人讲滇西边防的故事。他没想到,直线距离仅70公里的“进山路”,徒步得走7天。墨脱的遥远,超出了周国仁的想象。
周国仁是边防营最老的兵。墨脱边防一条条靠人脚、马蹄踩踏出来的巡逻路,他走了20年。巡逻途中“马死人亡”的事他听过不少。
那年5月,多雄拉山的开山季提前了两个月,给边防营运送给养的任务随之展开。时任副连长张洪万带队背着给养翻越多雄拉山。大家刚爬到半山腰,一场暴风雪猝然来袭。
有着20余次带队“闯关”经验的张洪万,带领巡逻队在风雪中跋涉两个多小时。即将抵达多雄拉山口时,他发现有6名新战士不见了踪影……
张洪万心急如焚。他将战友和物资安置在一个山洞内,便带领2名战士,转身走进茫茫雪原。20分钟后,张洪万找到了掉队的战友。正当他收拢人员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是雪崩,快向右撤!”眨眼间,张洪万被积雪吞噬。
“我的新兵班长伍伟,就是被救下的6名战士中的一员。”周国仁说,每次讲起这件事,伍班长都眼含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