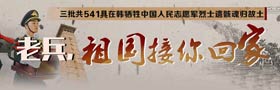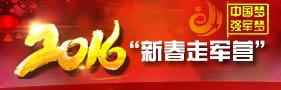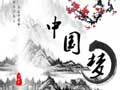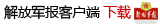又是一年清明节,每到这时都会想起很多逝去的人。

今年,在空工大每位学员的记忆里,又多了一个名字,张鹏教员,因突发结核性脑膜炎而病逝,身高1米92,从教30年。因为教的是基础战术,皮肤从来都是黝黑的。
我与他并不相识,但现在他却成了我脑海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3月6日,点开朋友圈,张鹏去世的消息满满地刷屏了,有领导干部转发,有教员转发,也有新学员转发,甚至很多毕业多年的学员也纷纷转发。《最后的送别:张鹏教员,一路走好……》《天堂里继续大鹏展翅》,这两条的微信寄托了成千上万官兵无尽的哀思和泪水。
不同的跟帖、留言,相同的敬重、思念:“如果在古代,他一定就是常山赵子龙”“最喜欢张教员的那句话——要有精气神”“您教我射击时的认真我无法忘记,想您!”“看见操场就会想起您,愿您在天堂一路走好”……
每一条微信,阅读量都近10万。
张鹏从事的是军事基础课,在大家的认知里,这样的基础课很难取得大量的教研成果,也很难获得高等级的个人荣誉,唯一与专业课不同的就是带的学生会众多。
可就是这样一位普通教员,却得到了全校教、学员的认可和爱戴,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带着这个疑惑走进了空工大,希望能从众人零碎而深情的回忆中,认识他……

学员王美宏认识张教员是在一次射击训练课上,那是炎热的一个夏天,当时张教员替人代课,就是这一课,让王美宏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那堂课上,当学员都热得脱掉了训练服只穿个迷彩短袖时,他却依旧保持着挺拔的军姿,军容严整:武装外腰带扎得紧紧地、帽子压得低低的。那汗水早已湿透了他的迷彩,可他似乎什么也没感觉到,眼里只有学员的身影。学员营营长章声波回忆起张鹏教员时说,张教员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打靶课上,年近半百的张教员给学员教动作都是趴在学员身边,一个人一人、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他说,身材高大的张教员,站着是座峰,趴下是道岭。
2012年,军队院校调整改革。于年近五旬的张鹏而言,经历的不仅是一次单位改革,更是个人的转型。由于军事技能教研室人才紧缺,当时身为体育教员的张鹏,被调整进了这个陌生的领域。轻武器射击、共同条令,作为军人,张鹏都能迅速熟悉,但对于军事地形学,这种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说实话,张鹏当时心里是有点胆怯的:不是不想接,而是怕教不好,教得比别人差。
从“一无所知”到“胸有成竹”,从“不耻下问”到“讲课第一”,张鹏只用了半年。

张鹏的半年,是缠着比他小20岁的人追问不止的半年,是把军事地形学课本勾画成迷宫的半年。教材里地图上的字特别小,他看了一会就头晕眼涩,眼药水与教材的“混搭”,是他办公桌上的“标配”。教研部领导没有想到,被他请教过的同事也没有想到,仅仅只用了半年,张鹏的军事地形学就获得了学院讲课第一名,成为了这门课程名副其实的“大拿”。

整理张鹏遗物时,同事谢浩发现,最多的还是教案。甚至很多教案都是张鹏手写出来的。每次课后,他都会根据学员的反应,不断地对教案进行修改。同事纳闷了,都是老教案了,有什么好改的?张鹏笑笑说:“老东西要讲出新内容,学生才会爱听,爱学!”
和他共事多年的宫辉回忆说,办公室里共有四名同事,张鹏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但他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同事们来上班时,办公桌早被擦得干干净净,地板也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宫辉当时特别不好意思,说:“以后卫生你别管了,等我来了再拖吧。”张鹏笑笑说,“你孩子小,我孩子大了也没有什么事,就算给大家帮帮忙。”

就西方电影的“绿巨人”一样,张鹏总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在回兰州老家的路上,一辆夏利翻倒在逆向行驶的路边,很多车车视而不见,张鹏却停下车,果断地把翻倒的车玻璃砸开,救出了困在里面的司机……
张鹏篮球打得很好,在西安市篮球界小有名气,很多地方单位都向他抛出过“橄榄枝”。西安市新城区税务局局长王勇当年也“挖”过张鹏。王局长回忆说:“当时部队工资低,我多次挖他到我们单位,但他就是不舍得这身军装,每次头都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寒风拂动泪眼,痛悲战友长眠。
张鹏遗体从兰州向西安转运的那个晚上,教研部全体同事冒着寒风,在高速收费口等了三个小时,迎接这位英雄的归来。这次,他永远睡着了,同事们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了。
追悼会的那天,无论是阅历丰富的将校领导,还是涉世不深的普通学员,都哭得像个泪人。军人固然充满血性、意志坚强的群体,但他们内心也有柔软之处,只是未到动情时。
即将火化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提醒,赶紧剪掉张鹏身上所有带金属的物件。但作为老战友,训练部贾峻副部长还是小心翼翼地一个一个卸掉他的领花、资历牌、胸标、姓名牌。贾副部长知道,这是对张鹏最好的尊重。因为,这身军装,是张鹏的骄傲!
教员音容,凭厚德垂世,笑看人间纷飞多少桃李;弟子泣泪,当奋起图强,丹心永在传承讲台风采。
张教员,感谢有您,这个世界因为有您的存在而完美!愿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