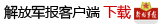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一名战士跑步训练归来。
- 6 -
如果换个心情,可以看到这一路的不少景致其实是“诗情画意”的。他们在轰鸣的水声中穿过竹林,绕过瀑布,跨过乱石,从五六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下经过。会与猴子、黄羊、野猪、松鼠和小熊猫打照面,会见到质地密实、刀枪难入的稀有树种红豆杉。头顶有看不到影子但歌喉动听的鸟儿,也有美貌惊人但叫不出名的鸟儿。
但是,那种对风光的好奇早在第一次巡逻中就消磨殆尽了,每个人提起这些路,都会使用一些描述炼狱的词语。因为等在前面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六连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牺牲者远多于此。在杨祥国出生那天,1984年的一天,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到此踏勘道路时心脏病发作,痛苦地拽着马尾死去。
所有烈士中,最年轻的看着像个孩子。2005年,19岁的古怒在巡逻途中摔下了悬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当地语言所说的“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古怒是杨祥国的同乡,比杨还要瘦小。杨祥国是他的班长,余刚是他的排长,但他们都因事缺席了那次巡逻。余刚正在昆明参加军校的考试,“我们有一个人没了”,他接到电话。他第一反应不是古怒,是“最不听话”、令他最不放心的一个兵。
是过桥时出了事。那里是一处湿气很重的陡壁,木桥和山石上生着青苔,下面看不见底。为防万一,过桥要一个一个来。古怒位于队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会神过桥的战友次仁珠杰所看不到的: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正从右侧滚来。
泥石流并不稀奇。“走着走着,碗大的、锅大的石头就下来了。”余刚说,“最好站在原地,看着石头往哪个方向(滚)。”
但这次来不及了,古怒冲过去推开了次仁珠杰,自己却被石头砸了下去。
他摔出不太远,人们找到他时,他仍有意识,但颅内出血,伤得很重。他死于归途。
他本来已进入回家倒计时,再过5个月他就会退役。那次巡逻出发前,他站在宿舍的楼梯转角处,对人说他再去最后一次巡逻。他还提议,这次回来,大家要开个小火锅,“烫个菜”。
最后的痛苦挣扎中,古怒力气很大,抬他的两个人也差点出事。那天带队的连队指导员殷永飞事后告诉余刚,如果这二人也摔下去,“老子不管了,也飞下去了”。
余刚至今耿耿于怀,他习惯在队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后面的就不会是古怒。
这是余刚第二次见到牺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个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罗国稳摔了下去。余刚当时是新兵。他记得,人们系着绳索下去寻找罗国稳,绳子放了七八十米,才发现他落在一棵树上,树尖刺破了他的心脏。
二人遇难之地,后来叫“舍身崖”。
舍己救人的古怒被追记了一等功,他穿过的军服进了团史馆。人们为他穿上新衣,把他葬在营区一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永远眺望他的连和他的路。
而那位司令员的纪念碑,则树在通往连队的公路一侧,碑上顶着红星,裹着哈达。余刚路过时习惯下车敬上三支香烟,祈求昨天的司令庇佑今天的部属。
“有些人会到祖坟上许愿保佑升官发财,我从来没有许过这个愿。”余刚说,他一直都在祈祷兄弟们“健康平安稳定”。
有时,余刚会在古怒墓前对新兵感慨:“看看我们古怒,永远在这个地方了。”
除了余刚和杨祥国,与古怒有过交集的战友都已离开了这个连队,但这个小个子仍常被提起。新兵来时要认识他,老兵走时要向他告别。17岁的新兵匡扬武记得,他们报到的第二天,就被带去给古怒扫墓。
为表心诚,扫墓时每人自掏腰包买点祭品。年轻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意,水果、饼干、鸡翅、薯片、花生、不同品牌的可乐,酸奶要插上吸管。无论是否抽烟,人人敬三支烟,香烟插在旧弹壳里固定。
余刚还会拍下照片,发给古怒的家人。驻军始终与重庆这家人保持着联系。杨祥国与4位退伍老兵多年来有个约定,只要他休假回重庆,就同去古家看望。
古怒的母亲最初连续三年来扫墓,2015年又来过一次,向众人分发了她亲手做的鞋垫。儿子出事十年了,她仍坚持到遇难处祭奠,拉着团政委杨守宝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等到回归平静,人们听到她说:“我养了个好儿子。”
- 7 -
古怒葬礼几个月后,他的指导员殷永飞被哨兵发现半夜晕倒在水沟里。他清醒后告诉别人,自己起夜时听到古怒在喊他,感觉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但每张脸都是古怒的脸。
失去古怒是殷永飞“终生的遗憾”。余刚不确定他今天是否走出了阴影。据他所知,殷永飞给古家寄过冬虫夏草等药材。殷后来调离了连队,然后又在2017年彻底告别了军营。临走之前,他又一次去了古怒的墓地,嘱咐余刚不要再像他一样“把兵带没了”,嘱咐人们多去看看古怒。
实际上,那场事故给整个连队都投下过阴影。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杨祥国说,不知是谁发现了巧合:从1984年算起,每七年牺牲一人,“七年之痒”。
余刚也承认,大家经过古怒出事地时会紧张。有一次,距离那里大约500米的位置,一个士兵踩滑,摔出十多米。余刚远远看到他一动不动,第一反应是“完了,又一个”。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看到那人眼睛很亮,但说不出话,直至获救仍不知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他感到“压力空前大”,每次巡逻选人,挑了又挑,慎之又慎。
在刘东洋记忆里,到了2012年,大家普遍有点担心,他不认为这是迷信,毕竟那种巧合让人“难免心里嘀咕”。那年年底,最后一次巡逻结束时,他松了一口气。
当2012年的日历终于翻到尽头,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一个关于时间的“魔咒”被时间打破了,它是无稽之谈,却带来过真实的阴影。
但即便如此,人们报名巡逻时仍争先恐后。平时表现突出的才会被选中,不止一人落选后越级找营长诉苦,“为什么又不让我去?”
余刚试着找出一些安慰性的借口,比如“你个子太小了”。
“难道我个子太小了是我的错吗?”
还有一位叫胡玺乾的士兵,被调到了县城,总觉得哪儿不舒服,找到机会向团长申请,又调了回来。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遇到巡逻,马上斗志就来了,火苗就燃起来了。平时你没看他怎么样。”连队现任指导员母科说,这是体现一个军人价值的时候,留守者心里会窝火。
母科生于1988年,入大学时就是国防生计划挑选的后备军官。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是“for honor(荣誉导向)”,而雇佣军制度是“for money(金钱导向)”。
死神其实一直离得不远。余刚就曾在悬崖上救过人,最终两人抓住绳子悬在半空,死里逃生。
如果摔下去——“那么今天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就是别人了。”
在后来者眼中富于传奇色彩的杨祥国,曾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3次救过人,也被人救过。他摔下被树接住过,下面只看得到细细的水线。战友张威被他救过多次。有一次张威丢了墨镜——这可能导致雪盲症进而遇险,杨祥国与他轮流戴一副墨镜,手拉着手行军。
“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杨祥国说,跟这些人平时连电话都不常打,但彼此是在心里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相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