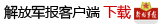- 13 -
今天的人已无法设想营地当年的苦,光是限时使用智能手机已让他们难受不已。“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低头族’,”李声松说,每个人都要克服离开手机心里“发痒”这一关。
连队太过闭塞,典型的“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每个年代的人都需要适应隔绝所带来的孤独,孤独从没离开,只是不停地更换表现形式。杨祥国记得,没来多久自己就能够仅凭味道和脚步,判断身后走来的是谁。所有人都能背诵电视新闻前播放的广告词,实在“找不到事耍了”。
当年,为了照顾新兵,连队不安排他们外出背物资,但大家总是抢着去,可以趁机见见外人。
“很多人(整个服役期间)没见过连队以外的人。”杨祥国解释,那种心情是,“希望见到陌生人,又怕见到陌生人。”
谷毅认为,部队越偏僻,人的语言能力越弱。见到外人都想“多看两眼”,但未必会打招呼。多年前,他去过一个连队,那里的人提醒他晚上用棉衣蒙住头。他奇怪但照做了。睡梦中,有老鼠跳上了床。他问为什么不赶跑老鼠,回答是,“习惯了,反正大家都在一起”。
在鸿雁传书的年代,杨祥国记得,一人收信全班都很高兴,收信人常被要求当众念信。无聊时,有人念给狗听。
这些人对动物有战友般的感情。连队养了十几条狗,它们一代一代在此繁衍。一只名叫旺财的狗垂垂老矣之际跑了出去,不知死在什么地方,让人伤感不已。
那些隔绝程度更高的高山哨所里,总是存在更加不可思议的孤独和眷恋。多年以前,一位军人生了重病,临终心愿是再回一次他放过哨的地方。人们抱他爬上了那个“伸手把天抓”的哨所,当时他的体重只剩30多公斤。
曾经在一个云雾缭绕的哨所,谷毅掀开被褥看到,人民币一张一张铺在床板上,都是领到的津贴。纸币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此类环境下,再内向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与人说话。白玛坚增说,有些人刚到时跟人相处不来,两三年后完全变了个人。而唐银相信,多数人都会成为开朗型,因为大家总是想法让不爱说话的人开口,加入到“吹牛”聊天之中。
一个笑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再使用一遍,“一个话题上个月‘吹’了,隔两三个月又‘吹’出来了。”
每个人休假时都感到,自己落后于语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们说什么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刘东洋说。李声松与大学同学聊天,这些人随时蹦一个新词、一个新“梗”出来,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面流行的一个“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才会在这里生效。
“一直在边防连队当兵的人,都很单纯很纯洁。我们这边的人看起来很傻,眼神不一样。”白玛坚增说,他在军校里遇上其他地区的军人,自我感觉比人家能老上十岁。
他还记得,曾有一位女干部来到连队,一下车给了在场者每人一个拥抱,大家都很感动——平时见到异性的概率很低,偶尔有军嫂来探亲,大家都想看一眼,“纯粹的向往,没有什么邪念”。
医院派来的体检团队,女医生和女护士永远最受欢迎。胆子大些的排队量完血压后就混到队尾再量一次,可以多些接触。
- 14 -

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一名战士收到家里寄来的快递。
每周两次开着皮卡车到来的邮政送货员最清楚一点:互联网及快递业的繁荣,密切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车上的包裹总在增加。
那些发自老家、经过两家以上快递企业转手才最终到来的雪饼、薯片、辣条、奶茶和乳酸菌饮料,证明收件人仍是妈妈眼中的孩子。
那辆旧皮卡帮一位在新疆做生意的父亲送来干果,替广东乡下的一位母亲捎来自制的红薯干。四川一家人寄来的是家乡特产的挂面和“八宝油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西藏一位母亲给儿子寄来了压缩干粮。通常来说,能收到什么取决于“跟爸妈报需求”,零食几乎一开箱就会被人哄笑着“宣示主权”。
一年里的多数时候,邮政送货员是能够进入营区仅有的外人。在深山里这个“铁打的营盘”,这是铁一般不变的事实之一。
这就是陇,一个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但同时顽固不变的地方。“流水的兵”不断更替,伙食从三菜一汤变成六菜一汤,新鲜蔬菜的供应更加充足,但罐头仍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库房里码放着包括回锅肉罐头和三味辣椒豆瓣在内的上百种罐头,麻辣茄子和炒素三丝罐头一直是公认最难吃的。
同样是伙食,种类变了,但口味没有变过。从食谱来看,这里的人呼吸着西藏的稀薄氧气,但活在四川辣椒的气味里。兵源地以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为主,四川话是通行方言,以至于受访时,余刚首先询问能否以四川话作答,他担心在普通话里会言不达意。当年他参军前,母亲对他提的另一条要求就是,即使在部队留不下也不要带一口“南腔北调”回家,她当然不会想到,儿子要去的地方完全杜绝了南腔北调的可能性。
瞬息万变的外界面前,陇保持了一种脱节的状态,这是它最大的不变量。它连看上去都像是那类“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神奇传说的发生地:日复一日,太阳透过雪山银顶,发出眩目的金光;白云或快或慢翻页,像山中飞出的经书;乌鸦一身漆黑,在常青的树木中间跳跃。河流喧哗着头也不回地奔过。
脱节使它具备了一些只有在一个大国的末梢才能看到的状态。大门外的杂货摊在这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顾客与摊贩之间也并非单纯的买卖关系。士兵们放心地把银行卡及密码交给摊贩,请对方帮忙去城里取钱,而现金通常除了杂货摊也别无去处。这里同时出售“北京牌”方便面和西双版纳的甘蔗肉,名目繁多的零食和饮料永远卖得最快。
除了做生意,摊贩还会帮人向家里寄回在部队得的奖状。一位江西籍士兵的母亲去世,连队拜托一位摊贩紧急把他送到了机场。
通过他们,打牙祭的士兵还可以从城里代购“德克士”快餐店的炸鸡。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炸鸡早就冷透,并且饱受摧残,但买家拎着袋子兴高采烈,仿佛拎回了整个热腾腾的城市生活。
与袋子里的温度一样,城市化的效应从远处传来,逐级衰减,在末梢的位置能够抓住的只是片段。
穿梭在城乡之间送来的快递袋里,一些东西像是走错了地方:卫生巾,可以垫到鞋里,让巡逻的双脚舒适一些;面膜,多半是探亲之前,这些年轻人为了让父母见到自己少一些沧桑,修复皮肤的徒劳尝试。
西藏军区干事晏良记得另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尝试:他的一个战友临时抱佛脚,从拉萨回家之前,走进了一家美容院。
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家美容院,能够去除地球“第三极”留给这些人“高原红”的烙印。天长日久,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伤口总是好得很慢,别处一个星期结痂的伤口,这里需要两个星期。刘东洋猜测,在高海拔地区,人体机能出现了下降。
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变化,医学影像能够拍到:肺动脉的增宽和右心室的增大。谷毅早年回到平原地区读军校,差点因为心率过缓而被拒绝。
一个不易察觉的变化,他们倒是最先感知到了:地球正在变暖。青藏高原是气象学家眼中的气候“放大器”,而这些人的身体最早对放大器发生感应。
老兵们都认为以前比现在冷。每时每刻,在看不到的地方,冰川在消融,雪线在上升。他们生冻疮的概率在降低,部分得益于条件的改善,但他们相信与气候有关。
官方数据证实“西藏增温强烈”。1961年至2013年,西藏的年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增温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过去30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年均减少约131平方公里。
余刚有一整套应对冻疮的可怕经验:长时间用温水浸泡,泡软后撕掉冻疮,涂上“高原护肤霜”,不停揉搓,再贴上创可贴。晾干皮肤,再浸入温水,撕掉创可贴,用夹子扯掉坏肉,再涂护肤霜。
冻疮曾经极具创意地每年拜访他的手脚和耳朵:手背开裂,指缝也开裂;横着开裂,也竖着开裂;直线开裂,也呈三角形开裂。有一年他去广西出差,当地武装部干部仅仅根据他的耳朵就推断,“你是西藏的吗?”
“西藏”意味着特殊的艰苦程度。国家针对“艰苦边远地区”部队服役者的优待政策里,地区分为几类,分配到驻五、六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一类岛屿“或者西藏部队”的,高定两个职务工资档次。
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在征兵办法里承诺,对“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优待金,按照标准的两倍发放。
晏良见过很多的西藏边防兵,容易识别的特征是他们通常皮肤更黑。由于缺乏维生素,长期生活在边防的人指甲是平的,有点像麻将牌的“白板”。耳朵冻烂的很可能刚从哨所下来。另一个特征是脱发,缺氧和压力的双重后果。
不满40岁的余刚摘下军帽,展示他的生平憾事之一:发际线后退了不少。山南军分区一个叫无名湖的哨所,一位2017年底退伍的士兵脱发严重,家人安排他相亲,他戴了假发,聊到高兴处,不小心把假发扯了下来。
“四个字:青春易老。”晏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