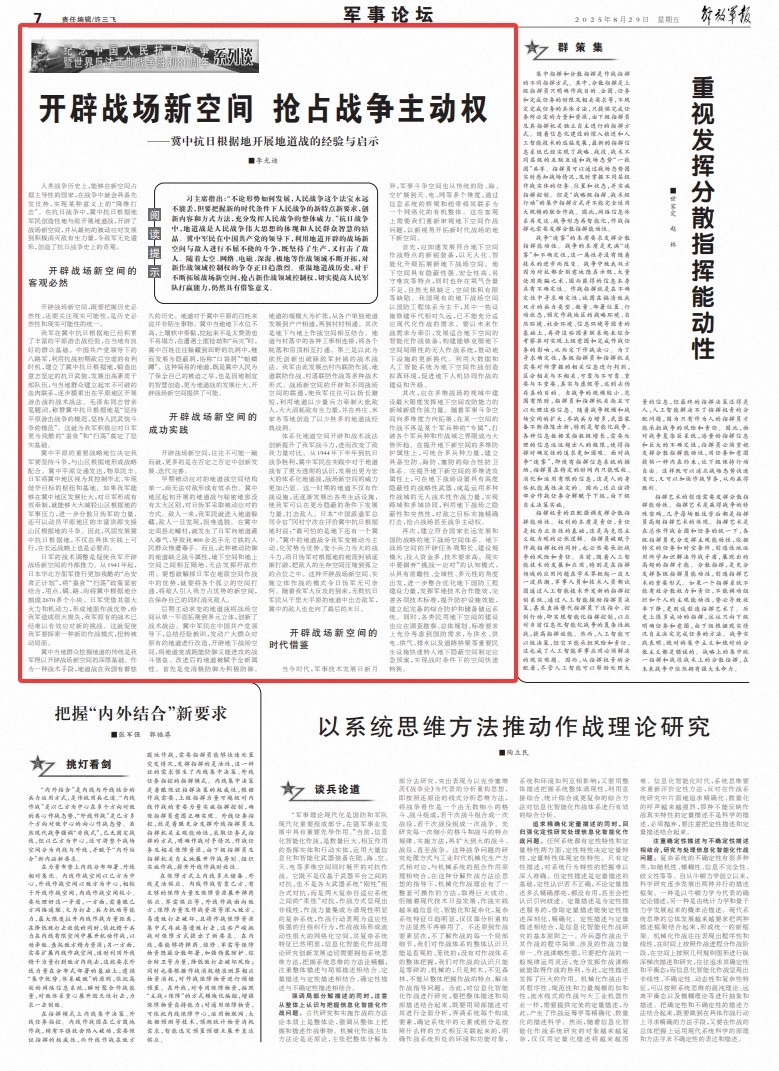开辟战场新空间 抢占战争主动权
——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地道战的经验与启示
■李光迪
阅读提示
习主席指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但要把握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创新内容和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抗日战争中,地道战是人民战争伟大思想的体现和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冀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开辟的战场新空间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既坚持了生产,又打击了敌人。随着太空、网络、电磁、深海、极地等作战领域不断开拓,对新作战领域控制权的争夺正日趋激烈。重温地道战历史,对于不断拓展战场新空间,抢占新作战领域控制权,切实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人类战争历史上,能够在新空间占据主导性的国家,在战争中就会具备先发优势,实现某种意义上的“降维打击”。在抗日战争中,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创造性地与敌开展地道战,开辟了战场新空间,并从最初的被动应对发展到积极消灭敌有生力量,令敌军无处遁形,创造了抗日战争史上的奇观。
开辟战场新空间的客观必然
开辟战场新空间,既要把握历史必然性,还要关注现实可能性,是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统一。
我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平原游击战经验,在当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利用抗战初期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锻造出意志坚定的抗日武装,发展出高素质干部队伍,与当地群众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逐步摸索出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战术战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题词,称赞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这就为我军积极应对日军更为残酷的“蚕食”和“扫荡”奠定了坚实基础。
冀中平原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我军要坚持斗争,与山区根据地形成战略配合。冀中平原交通发达,物阜民丰。日军将冀中地区视为其控制华北、实现侵华目标的枢纽和基地。如果我军能够在冀中地区发展壮大,对日军形成有效牵制,就能够大大减轻山区根据地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分散日伪军的力量,还可以动员平原地区的丰富资源支援山区根据地的斗争。因此,巩固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具体实践上可行,在长远战略上也是必要的。
日军的战术调整是促使我军开辟战场新空间的外部推力。从1941年起,日本华北方面军推行更加残酷的“治安肃正计划”,将“蚕食”“扫荡”政策紧密结合,用点、碉、路、沟将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日军凭借其强大火力和机动力,形成地面作战优势,给我军造成很大损失,我军原有的战术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新的挑战。这就促使我军要探索一种新的作战模式,扭转被动局面。
冀中当地群众挖掘地道的传统是我军得以开辟战场新空间的深厚基础。作为一种战术手段,地道战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地道对于冀中平原的百姓来说并非陌生事物。冀中当地地下水位不高,土壤软中带黏,挖起来不是太费劲也不易塌方,在遭遇土匪抢劫和“兵灾”时,冀中百姓往往躲藏到田野的坑洞中,继而发展为隐蔽洞,俗称“口袋洞”“蛤蟆蹲”。这种简易的地道,既是冀中人民为了保全自己的被迫之举,也是因地制宜的智慧创造,更为地道战的发展壮大、开辟战场新空间提供了可能。
开辟战场新空间的成功实践
开辟战场新空间,往往不可能一蹴而就,更多的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创新发展、迭代完善。
早期被动应对的地道战空间结构单一,尚无法对敌形成有效杀伤。冀中地区起初开展的地道战与秘密地窖没有太大区别,对日伪军采取被动应对的方式。敌人一来,我军民就进入地道躲藏,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在冀中定南县北疃村,就发生了日军向地道灌入毒气,导致我800余名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惨遭毒手。而且,此种被动防御的地道缺乏战斗属性,地下空间和地上空间之间相互隔绝,无法发挥歼敌作用。要想破解掉日军在地面空间作战中的优势,就要将各个孤立的空间打通,将敌人引入我方占优势的新空间,在保存自己的同时消灭敌人。
后期主动求变的地道战将战场空间从单一平面拓展到多元立体,创新了战术战法。冀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总结经验教训,发动广大群众对原有的地道进行改造,开辟地下战场空间,将地道变成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战斗堡垒。改进后的地道被赋予全新属性。首先是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地道的规模大为扩张,从各户单独地道发展到户户相通,再到村村相通。其次是地下与地上作战空间相互结合。地道与村落中的各种工事相连接,将各个院落和房顶相互打通。第三是以此为依托创新出破除敌军封锁的战术战法。我军由此发展出村内联防作战、地道联防作战、村落联防作战等多种战术形式。战场新空间的开辟和不同战场空间的联通,使我军往往可以扬长避短,利用地道以少量兵力牵制大批敌人,大大消耗敌有生力量,并在冉庄、米家务等地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地道战经典战例。
体系化地道空间开辟和战术战法创新提升了我军战斗力,进而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从1944年下半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冀中军民在实践中对于地道战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发展出更为宏大的体系化地道战,战场新空间的威力更加凸显。这一时期的地道不仅有作战设施,还逐渐发展出各类生活设施,使我军可以在更为隐蔽的条件下发展力量、打击敌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评价冀中抗日根据地时说:“最可怕的是地下还有一个冀中。”冀中的地道战令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变小兵力为大的战斗力,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地面封锁逐渐打破,把敌人的生存空间压缩到孤立的点位之中。这种开辟战场新空间、实施立体作战的模式令日伪军无可奈何。随着我军大反攻的到来,无数抗日军民从千里大平原的地道中出击敌军,冀中的敌人也走向了最后的末日。
开辟战场新空间的时代借鉴
当今时代,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军事斗争空间也从传统的陆、海、空扩展到天、电、网等多个维度,通过信息系统的桥梁和纽带将其联系为一个网络化的有机整体。这在客观上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地下空间作战问题,以新视角开拓新时代战场的地下新空间。
首先,应加速发展符合地下空间作战特点的新锐装备,以无人化、智能化升级拓展新地下战场空间。地下空间具有隐蔽性强、安全性高、易守难攻等特点,同时也存在氧气含量不足、自然光照缺乏、空间体积有限等缺陷。我国现有的地下战场空间以国防工程体系为主干,其中一些设施修建年代相对久远,已不能充分适应现代化作战的需求。要以未来作战需求为牵引,发展适合地下空间的智能化作战装备,构建能够克服地下空间局限性的无人作战系统,推动地下设施的更新换代。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系统为地下空间作战创造拟真环境,促进地下人机协同作战的建设和升级。
其次,应在多维战场的视域中建设最大限度发挥地下空间攻防能力的新域新质作战力量。随着军事斗争空间向多维度方向拓展,在某一空间的作战不再是某个军兵种的“专属”,打破各个军兵种和作战域之界限成为大势所趋。在提升地下新空间的多维防护属性上,可统合多兵种力量,建立具备空防、海防、塞防的综合性防卫体系。在提升地下新空间的多维进攻属性上,可在地下战场设置具有高度隐蔽性的战略性武器,或是运用多种作战域的无人战术性作战力量,实现跨域和多域协同,利用地下战场之隐蔽性和突然性,对敌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抢占战场甚至战争主动权。
再次,建立符合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防战略的地下战场空间体系。地下战场空间的开辟任务周期长、建设规模大、投入资金多、技术要求高。现实中要摒弃“挑战—应对”的认知模式,从具有前瞻性、全域性、多元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整合优化地下国防工程建设力量,发挥军地技术合作能效,完善各项技术标准,提升防护设施效能,建立起完备的综合防护和储备储运系统。同时,各类民用地下空间的建设也应在调查勘察、总体规划、标准要求上充分考虑到国防需求,为供水、供电、供气、排水以及道路桥梁等重要民生设施快速转入地下隐蔽空间制定应急预案,实现战时条件下的空间快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