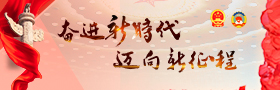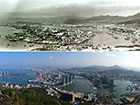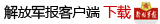4月12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在华中科技大学做了题为“道路与聚落——路学视角下的城乡结构变迁”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突飞猛进的“交通革命”使得中国社会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压缩,城乡之间的中间层级也随之消减,大区域、扁平化的“并联式”城乡格局将代替传统的“串联式”格局,成为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典型模式。
以下为周大鸣教授发言内容:

2017年12月9日,贵州遵义一山间乡道,从高空鸟瞰形同书法家用笔在山间写下的草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天我讲《道路与聚落:“路学”视域下的城乡结构变迁》。道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道路,但很少有人会去思考,更不会想着去从道路的视角做研究。一直以来,道路作为一种纯工程、纯设计的东西,没有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被研究,文献检索也查不到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其他的学科对道路的研究。这个对我们日常生活、工作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竟然没有太多人去关注,所以这些年我们开始做关于道路的研究。
道路和聚落是什么含义?第一个,道路是“过去供人马车通行所设计的路,两地之间的通道”,它是一种实体;第二个是一个比喻,用来比喻事物的发展,或为人处世所遵循的途径。聚落是人类个体居住地的总称,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就像我们现在要建“村村通”公路,道路总是要沟通各个聚落的。“路通财通”“要想富,先修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把道路看成一个纯粹的交通载体,而把它作为一个致富的工具。
当然,路对于城市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它们的修建可能会改变经济的格局,引起人流、物流等流动。举一个例子,我的家乡湘潭,在河运时代是湖南省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明清两代也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因为那时用木船做交通,湘潭适合做码头,而长沙不适合做码头,所以河运时代的长沙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商业中心。后来普通铁路修建,兴起了株洲。当时张之洞在武汉冶炼厂需要煤矿,在江西的萍乡发现了煤矿,从萍乡到武汉就需要一条铁路,先把煤矿从萍乡运到株洲,再从株洲下湘江运到武汉。后来粤汉铁路(现为京广线南段)的修建,也是修到株洲,因为铁路的修建,株洲很快超过湘潭。再后来,到了高铁时代,交通枢纽建在长沙,使长沙成为了湖南省无法取代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我想表达的是,交通的变化对城市的变化影响很大,比如湖南和江西。粤汉铁路最开始的设计经过江西,但在晚清,湖南人在朝廷做官的比较多,所以很多官员向朝廷建议这条铁路应该经过湖南。谭嗣同给光绪皇帝写了好几份折子说,铁路经过湖南有怎样的好处。可见,一条道路的修建其背后明显有政治、权力的博弈。随着粤汉铁路的修建,周边城市也逐渐兴起,但江西却被边缘化了——过去江西是很重要的通道,但有了铁路后,铁路成了一个大动脉,像毛泽东的一首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这讲的是长江和京广线,从中可以看到铁路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