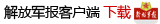历史镜鉴:中外军队的兴盛与衰败之谜
习主席指出,历史上不少军队在和平环境下耽于安乐、麻痹涣散,结果被和平打败,被自己打败。回溯历史长河,展望古今中外,战争与和平始终是贯穿其间的两条主线。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战争并非“绝对的坏事”,和平也不是只有好的一面。正如美国学者爱·麦·伯恩斯所说,战争是“世界上仅有的卫生术、高贵的英雄主义浴场”,和平将使一个民族“沉睡于懒惰的利己主义和沉迷于口腹饕餮的欢乐”。环顾跌宕起伏的世界军事史,和平积弊往往是一支军队从“其兴也勃焉”转向“其亡也忽焉”的罪魁祸首。
一、可怕之瘴,毁掉多少雄师劲旅
古今中外军队似乎都自带“系统漏洞”,谁也不具备对和平病毒的天然免疫力。
在染上“和平病”这个问题上,最富戏剧性的就是中国古代宋军、辽军、西夏军、金军、蒙古军的“前赴后继”。宋朝疆域初步确定之后,统治集团汲取中唐以来地方割据的教训,以文驭武,自我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文恬武嬉之风日盛一日。与辽、夏交战时,宋军再也没有当年“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霸气,前线将领必须严格根据皇帝战前颁布的阵图指挥作战,结果屡屡失利;西夏初期“以兵马为先务”,与周边交战几无败绩,然而等到国境安宁,统治集团“崇儒尚文”,兵政日弛,最终烟消云散;辽国号“契丹”,意为“镔铁”,也经不起太平日子的消蚀。在与宋国和平互市的一百多年里,辽军迅速从草原雄鹰变成瘟鸡,以致于公元1114年,辽帝亲率七十万大军东征,却被寥寥两万女真士兵杀得尸横遍野;女真族生来尚武勇猛,定国号为“金”,寓意要比“镔铁”更长久。但自走出白山黑水之后,女真人还是步了辽夏后尘。当蒙古铁蹄一来,金军便落花流水。蒙古军队虽不肯汉化,却也抵不住“和平病”的浸染,入主中原不到百年就被赶回大漠。
多少“前车之覆”都换不来“后车之鉴”。摆脱和平积弊与和平环境之间宿命般的纠缠,绝非易事。许多军队刚品尝到和平的滋味,鼓角铮鸣犹在耳边回响,“和平病”就开始酝酿,只需短短十多年或者数十年的发酵,曾经的英雄气概便消磨殆尽,魔幻般的蜕变。
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军队在赢得1859年意大利战争后,全欧洲都坚信法军是不可战胜的。但这种“迷信”却被自己打破。恩格斯说:“1870年的法军已不是1859年的法军了。盗用公款、营私舞弊和普遍的假公济私――形成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一切也已侵蚀了军队。”普法战争爆发时,法军“营地无法设立,因为没有人知帐幕在哪里;铁路运转时间表根本没有拟定;有些单位没有火炮,有些单位没有运输工具,有些没有救护设备;仓库中是空虚的,要塞中缺乏补给。”战争最终结局是,拿破仓三世和所属39名将军、10万士兵成了俘虏,法国的欧洲霸权地位被德国取代。
清朝统治者先后打造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都曾头顶清军主力的光环,怎奈谁也没有坚持多久。分析他们由盛转衰的周期,大致有一个相同的时长:30年。八旗军1644年入关后,便出现追求享乐的倾向,到1673年平定三藩之乱时,战斗力已严重衰退。清朝中期以前的历次战争,绿营兵都起着重要作用,到了1796年川楚教乱时,这支曾经的精锐已无力对付白莲教。湘军、淮军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一度能征善战,但到19世纪末已腐朽不堪。甲午战败后,新军登上历史舞台,不过,这支昔日以“十八斩”闻名天下的部队,也很快陷入军纪涣散、四分五裂的境地。
由此可见,“和平病”的侵袭,哪是什么“温水煮青蛙”,简直是坠崖式的沉沦!也有一些军队看似没有堕落得那么快,或是因为防治措施起到效果,延滞了发病的进程,或是因为实战检验来得晚了些,“败絮其中”被一时掩盖了起来。
陷入和平积弊泥潭不能自拔的军队,往往出现整体性的糜烂,从人员到装备,从灵魂到肌体,从上层到基层,方方面面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再强大的军队也终将元气耗尽、救无可救。当战争降临,惟剩一条死路。
当然,起死回生的机会还是有的;只不过须及早纠治,恶化到一定程度就成了绝症。明朝军队从宣宗时期开始浸染“和平病”,四境太平,兵卒一生不见打仗,军备逐渐废驰。张居正的富国强兵之策,给国家和军队打了一针强心剂,但万历年间对张居正的清算,使刚有起色的明军又继续败坏下去。以万历十五年罢官在家的戚继光凄怆死去为标志,这个帝国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到了崇祯皇帝,无论怎么励精图治,已无力回天。清史学家孟森评论:“思宗(崇祯帝)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物必自腐而后虫腐之,军必自毁而后敌毁之。罹患“和平病”的军队,看似亡于战场、亡于敌手,实则是自身种种沉疴积弊演化的结局。正像木乃伊接触到空气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生命力的军队作出了最后判决。过得了和平关,才过得了战争关。都说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殊不知和平也是对军人的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