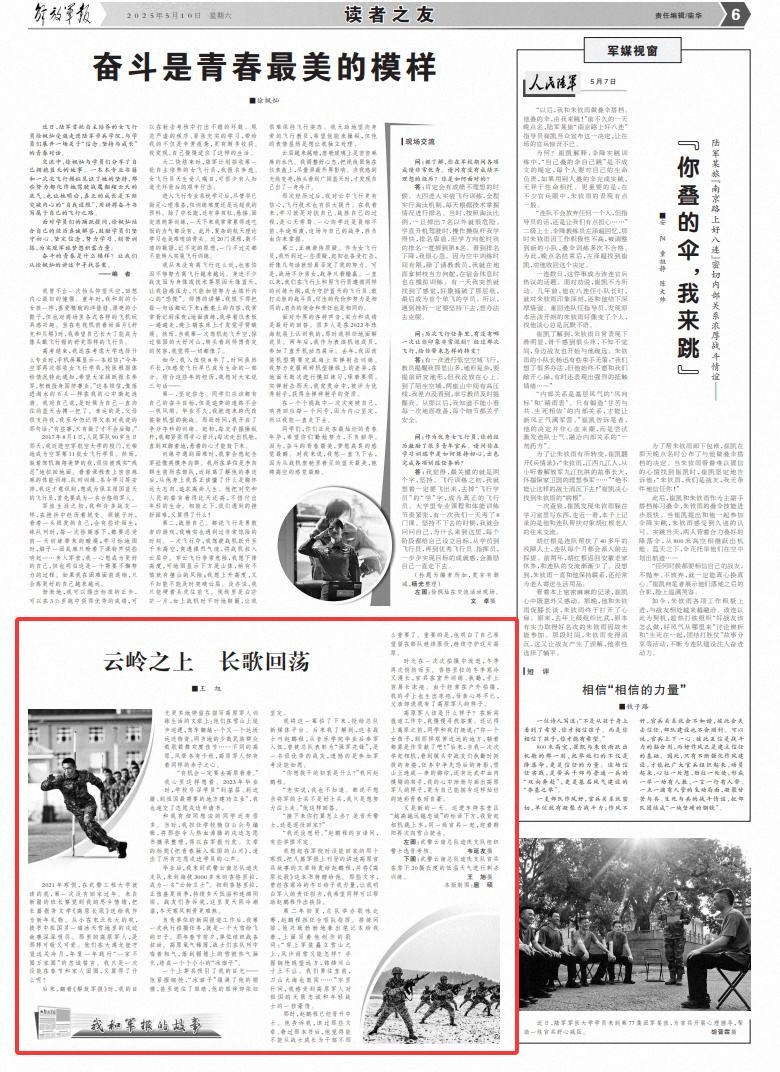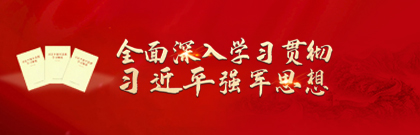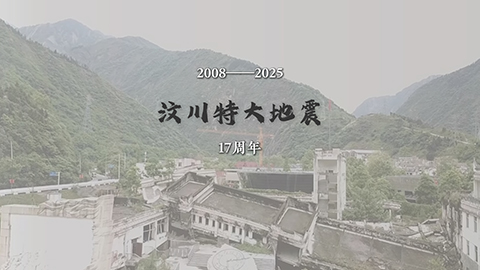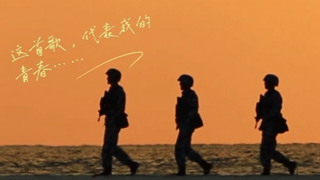云岭之上 长歌回荡
■王 旭
2021年寒假,在武警工程大学就读的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来自新疆的班长察觉到我的思乡情绪,把长篇报告文学《高原长歌》送给我作为新年礼物。从小在东北长大的我,被书中祖国另一端冰天雪地里的戍边故事深深吸引。那里的高原军人,是那样可敬又可爱。他们在大漠戈壁守望边关冷月,年复一年践行“一家不圆万家圆”的忠诚誓言。我只是一次没能在春节和家人团圆,又算得了什么呢?
后来,翻看《解放军报》时,我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描写高原军人训练生活的文章上:他们在雪山上徒步巡逻,驾车翻越一个又一个达坂运送物资,同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载歌载舞欢度佳节……不同的高原,风景各有千秋,高原军人却有着同样的赤子之心。
“有机会一定要去高原看看。”我心里这样想着。2023年毕业时,学校号召学员“到基层、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我也递交了志愿戍边申请书。
和我有相同想法的同学还有很多。当时,我担任学校微信公众号编辑,将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戍边志愿书摘录整理,得以在军报刊发。文章的标题《把青春融入祖国的山河》,道出了所有志愿戍边学员的心声。
毕业后,我来到武警云南总队迪庆支队,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香格里拉,成为一名“云岭卫士”。初到香格里拉,正值盛夏雨季,持续多天低温和连绵阴雨。战友们告诉我,这里夏天阴冷潮湿,冬天寒风刺骨更难熬。

武警云南总队迪庆支队组织警士选晋考核。韦延友 摄
负责单位的新闻报道工作后,我第一次执行拍摄任务,就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那年春节前夕,单位组织战备拉动。高原氧气稀薄,战士们在队列中喘着粗气,落到帽檐上的雪被热气融化,结成一个个小小的“冰溜子”。
一个上等兵吸引了我的目光——他紧握钢枪,“冰溜子”缀满了他的帽檐,甚至遮住了眼睛,他的眼神却依旧坚定。
我将这一幕拍了下来,投给总队新媒体平台。后来我了解到,这名战士叫赵鹏程,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参军入伍,曾被总队表彰为“强军先锋”,是一名很优秀的战友,遗憾的是参加军考没能如愿。
“你想提干的初衷是什么?”我问赵鹏程。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只是想努力往上走。”他这样回答。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是晋升警士,还是退役回家?”
“我还没想好。”赵鹏程的言语间,有些举棋不定。
我想起在军校时没能回家的那个寒假,把几篇军报上刊登的讲述高原官兵故事的文章转发给赵鹏程,并将《高原长歌》这本书转赠给他。那些文字,曾经在寒冷的冬日给予我力量,让我明白军人的责任担当,我希望同样可以帮助赵鹏程作出抉择。
第二年初夏,总队举办歌咏比赛,赵鹏程担任合唱队指挥。排练间隙,他兴致勃勃地拿出笔记本给我看,上面写着他创作的歌词:“穿上军装矗立雪山之上,风沙雨雪又能怎样?手握钢枪眺望远方,锦绣河山寸土不让。我们勇往直前,刀山火海也敢闯……”字里行间,我感受到高原军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年轻战士的一腔豪情。
那时,赵鹏程已经晋升中士。他告诉我,读过那些文章、看过那本书后,他觉得能不能从战士成长为干部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己希望留在部队继续服役,继续守护这片高原。
时光在一次次拍摄中流逝,冬季再次悄然而至。香格里拉的冬季寒冷又漫长,官兵在室外训练、执勤,手上容易长冻疮。由于经常在户外拍摄,我的手上也生出冻疮,母亲心疼不已,父亲却说我有了高原军人的样子。

武警云南总队迪庆支队官兵在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天气进行刺杀训练。王旭 摄
高原军人该是什么样子?在新闻报道工作中,我慢慢寻找答案。还记得上高原之前,同学和我打趣说:“你一个女孩子,到那样艰苦边远的地方,躺着都算是作贡献了吧!”后来,当我一次次举起相机,看到镜头中战友们执勤时挺拔的身姿,任务中争先恐后的身影,雪山上连成一串的脚印,还有比武中血肉模糊的双手,我的心中渐渐勾画出高原军人的样子,更为自己能拥有这样灿烂的迷彩青春而自豪。
又是新的一天。巡逻车停在营区“越高越远越忠诚”的标语下方,我背起相机跳上车,同一线官兵一起,迎着朝阳再次向雪山驶去。
本版制图:扈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