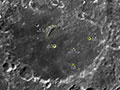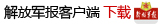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的世界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人们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感受到,这是一个让人充满了期待的快速变动时代,却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代。和平合作、改革创新、开放融通的潮流强劲,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互利共赢深得人心,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不断抬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依然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和应对这一复杂世界历史局面的唯一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各国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已然形成。这是我们今天解决发展问题的出发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仅靠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发展问题。在存在着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不是在一国之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世界市场的需求是每一个国家发展的持久动力,如果世界市场的需求长期萎缩,经济一直低迷,一个国家很难独善其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力、资金和人才的流动、调整和布局都是全球性的,在一国范围内无法实现生产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单独面对和驾驭新科技革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靠一国之力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发展风险。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维护世界和平不仅需要各国努力,还要形成和平共处的国际准则、解决国际争端的谈判机制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权威国际组织。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各国共同承担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解决生态危机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人口、贫困、暴恐等与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没有各国的相互配合、协调行动,都无法真正解决。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同上书,第477页)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展现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发展趋势,因而日益成为检验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优劣的尺度。中国在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展现了经济全球化不受资本主义狭隘利益羁绊的客观趋势。
顺应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尽管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不能回避,更不能抗拒,必须顺应;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被动顺应,更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积极引领。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利益难以合理分享,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则要加倍承担。如何在融入世界发展、抓住历史机遇而又不被西方国家吃掉,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
对于融入世界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困难在于抵御西方国家控制、捍卫自身利益的手段太少。应当承认,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它们要获得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权利,必然要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奋斗过程。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只是阶段性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体现了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趋势。从长远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必定属于世界人民。因此,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发展,善于抓住有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机遇,逐渐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出困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发展中国家要扭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弱势地位,关键在于主动面对。必须认清历史大势,明确发展出路,勇敢地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不怕呛水,不惧风浪,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必须把奋斗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在辛劳付出中壮大自己,在互惠互利中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18年5月1日)资本任性逐利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会自动让位于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由少数国家、甚至一个国家说了算的不公平的国际格局,不会自动改善为世界各国平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我们只有团结起来面对困难,作出最大的努力奋斗,才能最终战胜困难,开创历史的光明前景。
“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7页)我们坚信,随着处于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