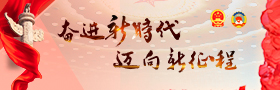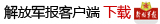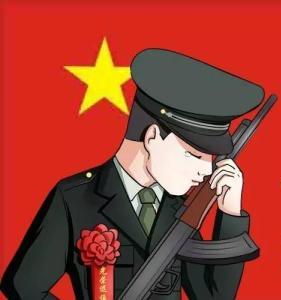
3、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国家设立了具有权威性的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机构,请您介绍一下国外这方面的主要经验做法。
郝万禄:应该说,梳理总结外国退役军人待遇保障管理的主要特点和共同规律,对于推进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概括地讲,国外的经验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退役军人待遇保障相对优厚。
许多国家明确,凡达到领取退役养老金条件的人,无论其重新就业还是领取养老金,都以退役养老金作为基数获得收入,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达到年限的退役军人无论今后的去向如何,待遇水平能够实现底线公平。保留服现役时的部分福利待遇,比如在医疗保障上,很多国家都规定退役军人可以继续在军队的医疗系统就医,享受免费医疗,从而保持现役时的医疗保障水平。一些国家还设有退伍军人公墓,专门负责退役军人的死亡安葬、纪念等事宜。
第二,退役军人待遇与服役贡献直接挂钩。
外军以优厚的现役待遇为基础,通过设置三条界限,即最低服役年限、长期服役年限、最高服役年龄合理设置现役与退役军人待遇差异。达到长期服役年限可以服役到最高年龄,有明确稳定的职业预期,可以得到高于其他职业的利益回报,有利于引导军官长期服役。
第三,重视退役军人再就业培训。
各国都非常重视对退役军人的再就业培训,帮助其尽快适应新职位的要求,而且越是发达国家,越重视对退役军人的培训,比如英国对退役军人的就业培训形式多样,既有军内培训,也有军外学习,既有离职前的培训,也有退役后的训练,为退役军人的再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现役退役人员待遇关系相对合理。
外军现役人员的工资水平一般定位较高,为确保使真正具有能力并确实在岗位做出贡献的人员享有相应的待遇,外军一般以合理的待遇差距为梯度,科学平衡现役与退役人员之间的待遇关系,以充分发挥待遇的激励导向作用。现役与退役人员之间适度的待遇差异,既满足了退役军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有利于引导现役人员安心长期服役。
第五,退役待遇管理体制完善。
把退役军人的安置管理纳入政府职责之中,并建立相应的机构承担这项工作,是许多国家退役军人安置管理制度的共同之处。许多国家的退役军人安置管理机构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组织系统,如美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是该国政府中仅次于国防部的第二大内阁部,并在各军种部设立“退伍服务办公室”。有些国家在民间设立非政府性质的协助退役军人就业的社会团体,如退役军人就业联络部、退役军人协会等,及时协调解决退役军人面临的问题,对改善退役军人政治和经济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4、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是一项开创性工作,从前瞻性的角度来看,您有何建议?
郝万禄:任何一项体制改革,都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定力”。如果我们的改革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定力”,可能会影响改革的终极效果。在这种背景下,关键要统一思想,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解观念问题,就是要树立“大机构观”,突破就退役谈退役的思维模式,把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从民族、国家、军队的视角来思考。
从待遇管理保障角度来讲,我提出“4+4”工作指导模式。
从目标定位来看,我认为要把握好“4个更加”:
一是设计理念更加科学。
坚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相配套,使退役军人与现役军人、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和谐互动、利益均衡的特定关系,实现退役军人从军队系统到社会系统的平稳过渡和有序发展。
二是保障范围更加合理。
适应独生子女成为退役官兵主体客观态势,以及军事职业特殊奉献,丰富拓展保障对象,推动政策优待范围由惠及退役军人和配偶子女为主向家庭成员全员覆盖延伸,确保他们前方有激情、后方无顾虑。
三是待遇水平更加优厚。
始终保持军事职业待遇比较优势,通过开展惠军工程、拥军优属、家庭援助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比如完善政治优待制度,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加完善的政治优待,增加对退役军人的精神抚慰,使其退役后仍能享有同样社会尊重;完善家属优待制度,帮助退役军人及其整个家庭在职业环境转换中实现平稳过渡等。
四是法规体系更加完善。
打破管理保障政策“零敲碎打”的传统做法,抓住全面深化改革契机,总体筹划、体系设计、衔接配套,推动退役军人管理法规制度建设由零散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变。
从管理保障来看,要实现“4个转变”:
在保障方式上,由转业安置保障为主向退役安置保障为主转变,对退役军人安置保障立足于“退役”,不再强调“转业”,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无限责任”问题。
在保障内容上,由国家“大包”向主要负责基本生活待遇和提高就业能力转变,就是国家不能“大包大揽”,要提高“包”的层次和水平。
在待遇标准上,由差别多元向公平规范转变,目前受安置方式和安置去向等条件的影响造成待遇标准差别多元,解决这个问题,应实现各类退役军人待遇标准公平规范。
在政策制度上,由依靠行政制度向依靠法规制度转变,使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