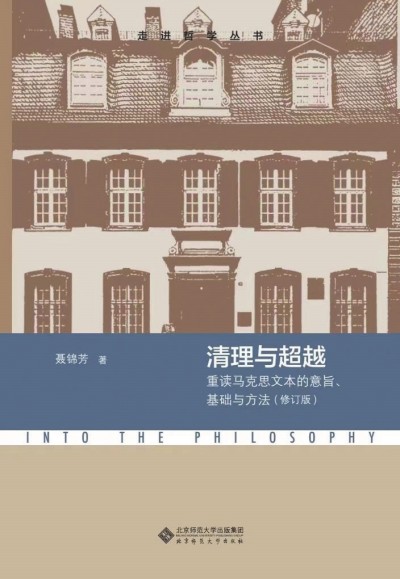
▲《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修订版)》,聂锦芳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166.00元
马克思文本研究20年:变与不变
■聂锦芳
2000年5月5日,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我当时作为中心秘书,参与了这一机构的酝酿、筹建、创办和后续运行的完整过程,特别是全部文献资料的搜集、购买、整理工作,基本上是由我一人承担的。这项举措旨在传承和发扬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注重文本、文献和思想史的传统,推动新的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无疑,它对于我的研究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清理与超越》一书就是我在梳理和考辨相关文献、反省既往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成果,于2002—2004年写作完成,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光荏苒,如今近二十年过去了,仍有研究者提及此书,更有不少学生做论文时会参考、引用书中的材料和观点。由于纸质书在市面上早已经售罄,有人便在网上留言,希望能够再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顺应读者的呼吁,邀我进行修订,并纳入“走进哲学丛书”。我在寒假期间完成了这一工作,谨将具体情况叙述如下:
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发生的“苏东事件”,以及随后不久便爆发的资本动荡和金融危机,使得“重读马克思”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重要的思想潮流。而在国内学术界,进入21世纪以来,文本解读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路向,藉此打破了与国外马克思文本编辑和“马克思学”研究的隔离状态。最近二十年来,可以说是马克思文献编辑、出版和研究相当活跃的时期,一大批经过新的考证的文献及研究成果问世,特别是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全部出齐、2017年MEGA第一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2022年新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等陆续刊布,构成马克思文献编研史上一块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为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阐释和评价打开了广阔的天地。
如此密集的文献材料和大量考证成果使得20年前写作此书时我掌握的相关信息或者显得过时,或者存在遗漏,或者过于简单,还有的有明显的错误,更多的则需要进行完善。为此,我将原书第一章《马克思文稿的构成及其命运》中的第三、四节合并为“马克思重要文本的刊布、流传和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将第二章《马克思著述知多少?》中的第四节《MEGA2已经出版的卷次及其收文情形》经过大量补充、校订后挪入,作为第一章的第四节。至于第二章的其他内容我均删除了,基本的考虑是,随着新文稿不断被发现,使得当初我试图以“部”或“篇”为单位、从“书志学”(bibliography)方面对马克思著述的总体数目进行清理,既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其准确性更容易随时失效,这样这种统计工作的价值也就不大了。
原书第三章《马克思的文本世界》是篇幅和容量上最大的一章,我从马克思著述中挑选出5个大类、53篇自认为最为重要的文本,对其写作与出版情况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包括了:1.“少年习作5部,即中学文献(9份,1833—1835)、与父亲的通信(17封,1835—1838)、《献给燕妮的诗册》(3册,1836)、《献给父亲的诗册》(1837)以及保存在索菲娅纪念册和笔记本里的作品(1833—1837);2.笔记世界10部,即“古希腊晚期哲学笔记”(1838)、“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巴黎笔记”(1843—1845)、“布鲁塞尔笔记”(1845)、“曼彻斯特笔记”(1845)、“伦敦笔记”(1850—1853)、“美学笔记”(1857)、“人类学笔记”(1879—1882)、“历史学笔记”(1870年代末—1880年代初)和“数学手稿”(1881);3.时事评论17部,即《莱茵报》时期的政治评论(1842—1843)、“1842—1843年通信”、《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帕麦斯顿勋爵》(1853)、《革命的西班牙》(1854)、《18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福格特先生》(1860)、《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法兰西内战》(1871)、《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1872)、《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哥达纲领批判》(1875)、关于爱尔兰问题的一组文献(1867—1869)、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一组文献(1877、1881、1882);4.思想创构8部,即“博士论文”(1839—1841)、《黑格尔哲学批判》(1843)、《论犹太人问题》(1843)、《神圣家族》(184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哲学的贫困》(1847—1848)、《共产党宣言》(1847—848);5.写作《资本论》的历程11部,即“巴黎手稿”(1844)、《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4—184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7—1858年手稿”(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8—1859)、“1861—1863年手稿”(1861—1863)、《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1863—1867年手稿”(1863—1867)、《资本论》第一卷(1867、1972、1872—1875、1883、1887、1890)、《资本论》第二卷(1885)、《资本论》第三卷(1894)、《剩余价值学说史》(1905—1910)。
今天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这些篇目,我感到当初的选择依然是有道理的,比较适当而准确。但是,这只是选目上的简单考量,这次花费最大精力的修订,是对于这些著述所关涉的文献学问题的重新考察、梳理和完善。我分两种情况来处理:其中的49部(篇)我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们作为原书的第三章、现在作为第二章保留下来,所涉及的文献学信息,过时的替换,遗漏的补充,错误的修正,有的则是重写的;鉴于“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马克思文献学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与其他著述混在一起同等对待并不合适,所以我根据自己掌握的最新考证成果,单独设了五章一一进行了详尽的清理,这是本书最大部分的增补,占了全书近40%的内容。
此外,鉴于最近20年来马克思新文献的刊布促进了文本个案研究的进展,我当年所指称的“‘通行本’研究的遗漏”和“经典研究中的空白”的状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此,我删除了原书第四章《马克思文本的研究现状》的内容。原书第八章“目前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以本书第十章“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替换。
二
从今天的视角重新审视旧作,让我感到欣慰的,除了以上提及当初选目的眼光和判断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更有我关于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和方法的阐述,后者构成了此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尽管我知道,不仅在那个时期,就是就目前来说,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但经过这么多年的研读和思考、磨练和波折,我依然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它们是切中肯綮之论,非常重要和关键,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和落伍。
概而言之,我认为,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所写作的文本,显然绕不开20世纪所奠定的基础和积累。然而,我们今天仍感到有重新研究这些文本的必要,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过去的文本研究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鉴于过去的特殊情形,今天的重新解读必须突出强调如下几点:回到学术层面进行探讨;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文献资料,填补研究空白;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方式和理论架构,准确把握其思想;客观而公正地评估马克思学说的价值,为其合理定位。同时研究者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量,明确其界域和难度。
而围绕“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这一焦点,文本研究在方法论原则上关涉到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以及“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比较的前提、比较的态度与比较的逻辑等复杂问题。我在认真分析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阻障的基础上,着重阐明在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等矛盾之间既应保持融同与提升,又当有合理的区分与“必要的张力”;当过分强调现实性、思想性、主体性、个性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为矫枉过正,我们何妨呼唤对历史性、学术性、本真性与公度性的重视。
在文本个案的具体研究中,我主张,将版本考证、文本解读与思想阐释和评价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改变长期以来流行的做法,即面对一部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径直进行概括和阐释,而撇开对具体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过程、其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和内容的详尽考察、解读和分析,相反要尽可能深入到文本内部展开对具体语境、问题、文献、思想等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另一方面又要尽力避免走至另一极端,即把文本研究理解为单纯的文献资料的收集、考证、铺陈和罗列,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归结为做“历史考证版”(MEGA)编辑、把“文本学”等同于“文献学”,而是更看重在真实而权威的文献基础上的思想梳理、阐发和评论。
基于上述考量,本书对原书涉及文本研究意义和方法的内容,除了校订注释之外,我没有做修改。不仅如此,为了凸显这种思路和方式的传承和当代性,我增补了《五位“马克思学家”(法国的吕贝尔、美国的诺曼·莱文、苏联的奥伊泽尔曼和弗罗洛夫、美国的汤姆·洛克莫尔)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转变》两章,将原书第七章《“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一种新的研究动向》有关汤姆·洛克莫尔的内容并入前者,而将原书第六章《前苏联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特点》的内容,一部分删除,一部分插入新的第八章《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五种类型》(原书第五章)中,涉及马克思战友和学生的阐释和宣传、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文本研究中的“苏联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嫁接”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现”、“马克思学”的归旨和MEGA版的编纂原则。借此想表明,现在的我依然执著于二十年前形成的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当代方式”的理解,也算是一种“矢志不渝”吧。
三
但是,当修订完此书,看着桌子上面厚厚的打印稿,我心里并没有满足和轻松之感。严格说来,所谓“意旨”“基础”“方法”云云,还只属于文本研究的前提性思考和“清理”工作,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研究水准自然而直接的提升和“超越”。二十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这一领域涌现出一批成果,取得一些进展,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态势。我自己也和学生通力合作,在马克思诞辰200年之际推出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这样篇幅比较大的研究论著。尽管如此,必须承认,奠基于文献、历史和现实之上厚重的成果依然有限。举例说,2012年MEGA第二部分就已出齐,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国内外学界切实根据马克思留存下来的庞杂的原始手稿以及文献专家做出的大量考证成果而对《资本论》复杂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并置于20世纪资本社会发展、资本批判理论变迁和当代全球化严峻局面的宏大背景中检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著依然鲜见。正是基于这种考量,虽然自知学识和能力均很有限,我近年来一直围绕这一课题勉力深研,希冀与国内外同道一起攻关,力求在这一领域有所推进和突破。
关涉马克思的研究视域宏富,议题众多,仔细清理就会发现,《资本论》之外,尚有很多值得重新探究的方面。再随便举一个例子。这次重新修订书中所涉及的53部(篇)著述写作和研究状况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即马克思曾经想把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所有文章综合成一部有关时事问题的著作。应该说,这是他又一个“未完成”的夙愿。但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长达8年时间里、总共撰写的500多篇(组)文章大多保留下来了,但可惜的是,现在几乎没有研究者在新的时代氛围和全然变化了的社会境遇下再将其一一认真研读,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当时的时政观点、思想状况、与其前后工作的关系以及后续影响做出概括和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学说注重现实性和实践性,但错位的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对现实和实践时,表面上把握得通透和决绝,但实际上却不无困惑和迷茫,那么,马克思当年在特殊的人生境遇和理论探索中撰写的这些文章,不是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和范例吗? 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掌握他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事件的态度和看法,更从中体现出一个思考者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观照、透视、分析和介入现实,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到位、深邃和超越。
如此说,马克思文本、文献及其思想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