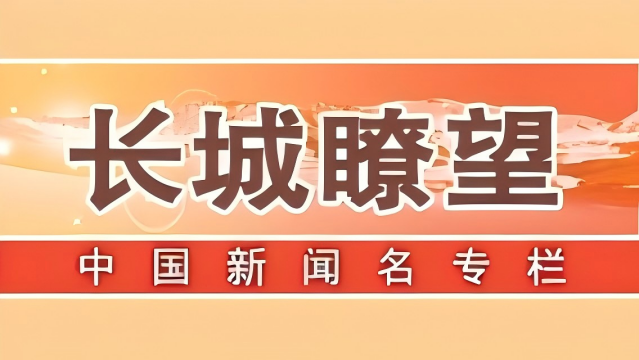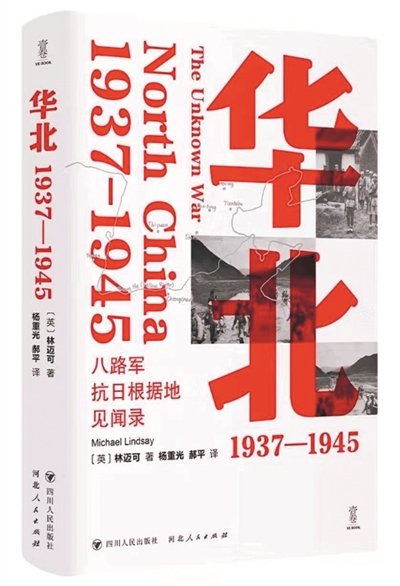
线索与提示
——再读《华北:1937—1945》有感
■赵诺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就是所谓“海外亲历者”。而在这些“海外亲历者”中,来自英国的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算是尤其特殊的一位。一方面,与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李敦白、斯诺、史沫特莱等人不同,出身英国贵族家庭的林迈可并不是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战士”,甚至原本连一位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都算不上,他受聘来燕京大学任教也更多缘于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但是,林迈可又比较直接、深入地参与到了抗日、革命工作当中,不仅曾长居晋察冀边区和延安,而且在根据地无线电通讯和对外宣传领域发挥过重要而特别的作用,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结下深厚友谊。由是观之,林迈可对自己在华经历的回顾,特别是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根据地的部分必然有较高价值。1987年,林迈可于1975年出版的回忆录(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由杨重光、郝平两位学者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2025年初再版。这本篇幅不算长的小册子堪称《西行漫记》外最受关注的“海外亲历者”回忆录之一。
这样一部中译本回忆录在近四十年间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有多重原因。一是因为林迈可在书中的很多回忆具体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日的奋斗历程,直接回应了所谓“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攻讦;二是因为译文准确、雅驯而不失鲜活。应该说,这两点原因是过去不少读者提到过的,也符合笔者十几年前读到第一版译本(《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时的印象。但在时代环境变化、学术视角转换的当下,再读2025年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译本《华北:1937—1945》,笔者深感其中仍有较多史料作为线索和提示可进一步挖掘、解读,在此可略举几点。
首先,“交通史”的视角。直观此书不难看出,作为一位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外国人,“转移”是这本回忆录里最突出的主题,林迈可也用基本上最多的篇幅记叙了他在路上的各种经历和见闻。那些译成中文的“羁旅之思”依然有几分浪漫:“那夜月光皎洁,夜行军不太困难,我们得绕着妙峰山走,因为山头上的庙宇里有些日本驻军。行到山的高处,回头可以看到远处北平城里的灯火闪烁。”(第95页)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一次次抵达实际并非易事,这些描述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构建地下交通网的具体线索。此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燕京大学到晋察冀根据地的“胜利大逃亡”,其实就是依托着地下党建立的“北平—妙峰山—田家庄(今属北京市门头沟区)”交通线。先前林迈可等人为八路军运送物资也是走的这条线路。过去我们笼统地知道,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城工部门在北平周边建立了四条秘密交通线,但对一些具体线路了解很有限。这次重读《华北:1937—1945》,根据林迈可的记述,结合他夫人李效黎的回忆录(《延安情》,李效黎著,肃宜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年版),便激活了过去笔者读过的一些零散史料,大致可以推断除前面这一条,还有几条线路:(1)北平—镇边城(今属河北怀来县);(2)北平—三家店(今属北京市门头沟区)—平西;(3)北平—松林店(今属河北涿州市)—张坊(今属北京市房山区)—平西。林迈可第一次去冀中见到吕正操将军走的是第二条路线,后来去平西根据地见到萧克将军应该走的就是第三条路线。而林迈可关于去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县及后来奔赴延安等等的记述,同样也提示我们注意党内地下交通史相关问题。
第二,“技术史”的视角。读过这本回忆录的读者,想必都会对林迈可在晋察冀和延安无线电通信技术改进上的贡献留有印象,但恐怕也仅仅停留于一般印象。笔者也是这次重读此新版译本才意识到林迈可的相关追忆中有不少重要信息。譬如,书中提到:“日本的密码员仅仅在1941年2月份破译了一次共产党的密码。从而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得以读懂共产党人的电文,而这正是共产党部队作战不利的一年。然而,共产党改编了它的密码,日本人直到战争结束也始终未能破译新编的密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密电码非常糟糕,日本人在整个战争时期对之都了如指掌。”(第120页)笔者初读时恐怕只感觉与国民党对比中国共产党人保密工作做得好,此番才与其他一些材料建立联系。回头看来,当时抗日根据地军民受到的重大损失很可能也与密电码被破译有一定关系。因为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开始要求大幅度整顿、减少基层单位的电台配备。1942年4月,中共中央曾严令军委和地方主管机关“严格整顿机密系统的电台,实行精简,彻底实现党军情机要台统一军队中,团一级的建制电台实行取消,由师旅控制一二架流动电台,按战斗需要临时派遣”。这一指示对通信兵和通信技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林迈可的记述,结合其他材料,便可大致明白,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此时已察觉到我们的无线通信系统存在极大风险。至于林迈可关于无线电通信的其他追忆,不同程度地提示我们去关注根据地通信设备采购渠道、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乃及未来新中国邮电领域组织人事源流等等问题。《华北:1937—1945》中有关技术史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无线电通信,还涉及到有线电话通信、炸药爆破、医疗卫生等等。而且,这本回忆录里还提到白求恩、柯棣华、班威廉等在八路军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外国专家,他们的参与、奋斗让抗日战争、中国革命在技术转移、技术交流层面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凸显了抗日战争、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环节。
第三,“知识史”的视角。沿着“技术史”问题的讨论,此处还想从“知识史”的角度谈谈《华北:1937—1945》中部分记述的史料价值。除了林迈可所忆给八路军送去关于炸药制造的教科书、在晋察冀根据地给大家教授无线电课程等,还有若干处线索值得注意。譬如,笔者在重读这本回忆录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多次谈到财经问题,甚至在绪论中他就不厌其烦地计算了根据地的税率。当然,很容易想到这是因为林迈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如果循此线索结合其他史料做一追问,我们就会发现,林迈可作为燕京大学教授,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或者说“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1938年初林迈可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后,除了负责主持导师制改革工作,主要开设了货币理论相关课程。他在课堂上即重点介绍了凯恩斯的相关学说。据燕大校内新闻称,林迈可在上课之余已在撰写一本名为《凯恩斯入门》的著作。又及,林迈可还提到自己因延安标准时间如何确定问题致信毛泽东,最终促成中共中央决定延安“使用其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第192页)。此事对当时延安的党员干部们了解时区制及标准时间问题有重要意义,在中国近现代“时间观念史”上也是一个重要节点。
此外,如果从“图像证史”的视角去看书中的那些很珍贵的照片,我们也能从中析出不少“服饰史”的材料,只是因笔者知识资源和文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具体讨论。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和知识的拓展积累,这本林迈可在五十余年前撰写、中国学者在三十八年前引入中文世界的回忆录,不仅没有没入尘烟,反而愈发受到广大读者和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主要缘于这本回忆录有非常丰富而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凡此种种,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读读此书确有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