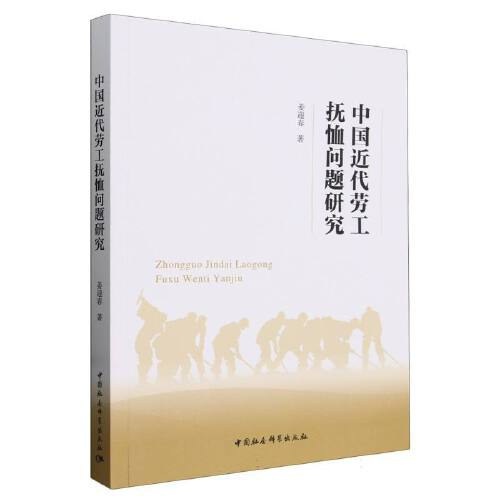
▲《中国近代劳工抚恤问题研究》,姜迎春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月,118.00元
追寻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轨迹
■吴文浩
姜迎春教授的著作《中国近代劳工抚恤问题研究》系统探讨近代中国劳工问题的发展脉络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轨迹,是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劳工抚恤问题研究》之成果,亦是其长期关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的又一代表性成果。
劳工抚恤问题之产生,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结果。本书所称之“劳工”,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语境中,就是指无产阶级。鸦片战争前,江南、岭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已有一定发展,出现了基本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地区开始出现产业工人。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新生产力趋于显著,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其中就包括从产业工人群体发展而来的早期无产阶级与自绅商群体发展而来的早期资产阶级,体现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进入大城市从事工业生产,这些日益脱离传统自然经济农业生产的工人群体,与乡村的联系趋于式微,意味着他们在遭遇突发事件时,回归乡村的可能性降低,只能寻求同在城市的群体、社会、政府的援助,抚恤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凸显。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问题,特别是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曾长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如作者所指出的,由于记录较少、资料零散,劳工抚恤问题的研究较为匮乏,少数的研究亦多流于相关条款的解读,而未将该问题置于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过程,乃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深层次因素进行考察。
劳工抚恤问题是近代中国工业化背景下社会变迁的缩影。无论是传统中国的手工业工人,还是近代早期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条件都是极端恶劣的,待遇亦差,甚至于因公伤残都得不到正式的抚恤,只能以临时性的救济措施获得一些帮助,但基本难以维持长期的生活。在工业化过程中,当时尚缺乏先进理论指导与严密组织指导的工人们,自发地对这一状况进行抗争,迫使政府与企业开始考虑劳工的抚恤问题,而西方社会保障思想与制度为近代中国提供了外部思想与制度参考。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法律政策等方面对工业发展的支持,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以及一战爆发后列强经济势力的短暂收缩,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使其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与之相伴生的是工业灾害、矿难频发,罹难工人人数激增,然而企业与资本家仍只是基于象征性的赔偿式抚恤,金额极低,使时人发出人命不如骡马之慨叹。同一时期,国际劳工组织亦对中国工人的状况表示关切,促使民国北京政府出台了《矿业条例》《暂行工厂通则》等法规,以保障伤残工人及亡故者遗族的生存权,但法律规定的最低抚恤金只是100日工资,完全无法维持受恤人的生活。这反映出漠视受恤人利益的观点与行为仍居于主流,一些团体以国家工业落后、产业不发达为由,为资本家贱视劳动者生命的行为涂脂抹粉,完全无意让劳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忍无可忍的工人自发起来斗争,其中涉及到抚恤问题的第一次大型罢工就发生在湖南水口山矿。这些斗争为1920年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奠定了一定基础,水口山矿后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蒋先云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
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推动,中国国内的劳工运动迅猛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政党出现,推动了工人的全国性联合,积极争取工人利益,并领导了陇海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等若干重大罢工运动,为工人争取到了因公伤亡3年的抚恤金及子弟袭职等权益。然而军阀政府难以容忍工人罢工运动的发展,对二七大罢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导致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促使中国共产党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并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之路线。
国民革命之一大旗帜是“扶助农工”,武汉国民政府曾颁布过切实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背弃了国民革命,但重视经济建设,工业化进展较大,同时也不得不关注工人的权益,积极促进劳资调和,借鉴苏联和西方法律、经验,制定了《工厂法》《劳动保险草案》《强制劳工保险草案》《简易人寿保险法》等涉及劳工抚恤的法律。这些法律将抚恤的试用范围从“凡含有危险性质或有害卫生者”,改为“凡用汽力电力水力发动机器之工厂”,明确了伤残亡故抚恤的标准,规定了雇佣期间工人因公治病的工厂绝对责任原则,但抚恤金仍是只能维持短期生活,没有保障长期生活的年恤金。由于资方的反对、租界内工厂外资工厂是否一体适用等争议,且政府执行力不足,国民政府同意将《工厂法》推迟至1931年8月1日,且效果不佳,仅在公营企业中得到较好的实施。如根据国民政府的调查,1933年湖南省符合《工厂法》规定的工厂有12家,但仅1家工厂落实了该法律。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逐步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公营企业得以扩张,《工厂法》的适用企业增加,接收抚恤的劳工群体人数亦随之扩张,事实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工抚恤水平。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使得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国民党政权深陷战争泥沼中,加上通货膨胀程度已至其无法收拾的地步,也就无力、无意对劳工抚恤问题投入资源,劳工抚恤的责任完全由企业承担。
与先行研究相比,该书有以下特点:
其一,不仅系统梳理了劳工抚恤制度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影响因素,更将宏观政策与微观个案相结合,基于较为翔实的数据,考察劳工抚恤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在制度方面,作者将近代中国的劳工抚恤定位为“过渡型抚恤”,并总结出政府缺位、以企业自为为主、劳工互助为根本等特点。在效果考察方面,作者以生活费指数为标准,探讨近代各个时期抚恤金的真实保障能力和作用,以了解抚恤制度的效度,得出劳工抚恤水平逐步提高的结论。
其二,完整揭示了传统劳工抚恤向现代劳工保障制度过渡的过程。作者结合民国时期政权更迭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歧,将民国时期的劳工抚恤制度分为发端(1911-1927)、初步形成(1927-1937)、艰难与应对(1937-1945)、自救与沉浮(1945-1949)四个发展阶段,展现了民国劳工抚恤理念方面由危难救急到短时间救恤、再到完全保障,手段方面由企业单方面的抚恤赔偿向企业、个人共责的互助保险转换,性质由传统的慰劳酬绩发展到近代的社会义务的发展,进而揭示了中国社会保障近代化的变迁史,体现出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工保障体系形成的内在逻辑。在劳工抚恤保险化趋势的研究中,作者将劳工抚恤的发展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相结合,提出了抚恤制度逐步向保险制度过渡的观点,不仅拓宽了劳工抚恤研究的视野,也为理解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三,史料与方法方面的进展。借助于大型民国数据库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地方、企业档案的整理公布等有利条件,民国劳工抚恤的资料较为丰富,作者投入了极大精力,并结合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方法,特别是引入了社会保障、社会冲突、阶级关系等社会学理论,拓展了劳工抚恤问题的研究视角,以社会保障的标准,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深入的归纳与解读,重点关注那些处于转型时期较为典型的事件和企业来分析,以图抓住劳工抚恤近代化的发展脉络,进而探究近代中国劳工抚恤的共性特点,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断,不仅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内容,也为解决当代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当然,学术研究是不断进步的,一本专著无法解决所有的相关问题。就笔者管窥之见,该书也存在以下两方面可以补充的内容: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民国时期劳工抚恤问题上的贡献需要进一步的阐释。书中在第二章及结论部分简要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但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革命党,亦是局部地区的执政党,尽管这些地方的工业可能不发达,劳工人数亦较少,但并非绝无仅有,作为以工人阶级政党自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其辖区内的劳工是何政策,有何抚恤与救助呢? 若能揭示这方面的内容,当为本书增色不少。
其次是作者已经注意到国际劳工运动及劳工组织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但在史料运用方面更多是利用中文资料,缺乏对国际组织档案资料以及租界内行政管理机构档案的运用,亦较少叙述租界内的劳工抚恤问题,从而未能揭示出中外在此问题上的冲突与协调。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列强以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落后为由,妄图维持治外法权,但是一旦中国制定并落实保障工人利益的《工厂法》,租界内工厂并不愿意落实,甚至一些外国资本家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保护劳工的法律,才愿意将工厂设置在中国。这些体现了近代中国主权与行政的不完整。
《近代中国劳工抚恤问题研究》一书通过详尽的史料、严谨的研究方法及独到的学术观点,系统地梳理了近代劳工抚恤制度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在劳工研究和社会保障研究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尽管在某些方面仍有改进的空间,但该书无疑为国内外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当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是一本值得深入研读的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