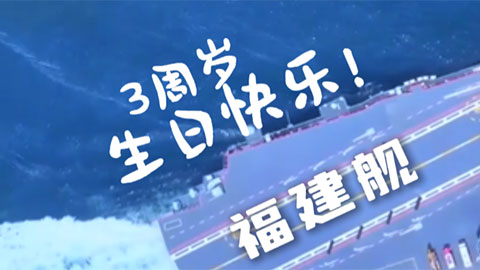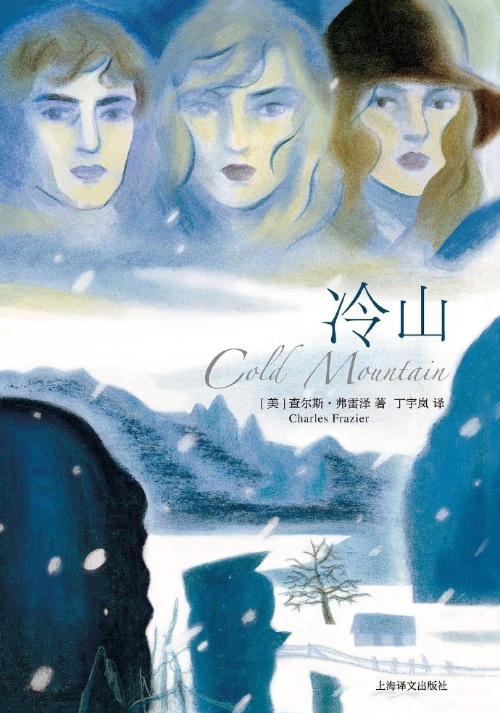
▲《冷山》,[美]查尔斯·弗雷泽著,丁宇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78.00元
在战火与荒野中寻找救赎的奥德赛
■冯新平
查尔斯·弗雷泽的处女作《冷山》自1997年问世以来,便以其诗意的语言、史诗般的叙事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成为美国南方文学的里程碑。这部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文学重构,更是一部关于孤独、救赎与自然之力的寓言。弗雷泽以冷峻而细腻的笔触,将主人公英曼的逃亡之旅与恋人艾达的生存抗争编织成一曲双重奏,在战火硝烟与荒野寂静之间,叩问人类如何于破碎中重建信仰。
南北战争常被简化为“自由与奴役”的宏大叙事,但《冷山》选择从战争的裂隙处切入,揭露其对人性的系统性摧毁。弗雷泽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笔法,描绘了彼得斯堡战役中“弹片如蝗虫般撕裂肉体”的炼狱场景,但真正令人战栗的并非血腥本身,而是暴力对人性纽带的瓦解——士兵们为争夺一具尸体上的靴子互相残杀,军官以“荣誉”之名驱赶新兵踏入机枪射程。这种书写呼应了蒂莫西·斯奈德对“血土”的论述:战争机器将人异化为可消耗的零件,而道德在生存本能前溃不成军。
英曼的逃亡因而具有双重意义:既是物理上逃离战场,更是精神上挣脱战争对人性的异化。当他穿越被焚毁的种植园、遭遇流寇洗劫的村庄时,每一步都在目睹“文明”面具的崩落。弗雷泽在此颠覆了传统的英雄叙事——英曼并非为崇高理想而战,他的旅程只是为了回归最原始的生存命题:活着回到冷山,回到艾达身边。
冷山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小说中超越性的精神图腾。这座隐匿于阿巴拉契亚山脉深处的山峰,在弗雷泽笔下成为对抗战争暴力的“自然圣殿”。英曼的归途充满荒野的隐喻:湍急的河流考验他的意志,暴风雪净化他的罪疚,而偶遇的隐士老人则以《奥德赛》般的智慧提醒他:“真正的家园不在某处,而在寻找的过程之中。”
与此平行,艾达在冷山农场的蜕变同样是一场自然启蒙。战争爆发前,她是依赖黑奴与父亲庇护的南方淑女;父亲病逝后,她在印第安女子鲁比的帮助下,学会播种、劈柴、驯养蜜蜂。弗雷泽在此重构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艾达通过双手与土地的直接对话,不仅获得了物质生存的能力,更在四季轮回中领悟到“人必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其主宰”。当她在雪夜独自接生小羊,这个场景超越了性别叙事的范畴,成为人类与自然重新缔约的仪式。
《冷山》的叙事结构暗合荷马史诗的框架,却赋予其现代性解构。英曼的逃亡是阳性的、线性的、充满外部威胁的奥德赛:他遭遇伪善的神父、食人的山民、追捕的民兵,每一次危机都在剥去他作为士兵的社会身份,迫使其直面最本真的自我。而艾达的留守则是阴性的、循环的、向内的珀涅罗珀之旅:她在荒废的果园中等待,却在等待中完成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蜕变。
二者的书信往来构成小说最动人的复调。英曼的信件充满对战争暴力的梦魇式描述:“我见过男人为了一撮烟草射杀同伴”;艾达的回信则渐次从闺阁哀愁转向土地的诗学:“今天我种下三行玉米,云雀在犁沟间筑巢”。这两种声音的对话,不仅消解了南北战争叙事中的性别壁垒,更暗示着救赎的可能——当男性在暴行中失语时,女性正通过重建与自然的联系,为破碎的世界提供疗愈的语法。
弗雷泽的文学基因中流淌着南方哥特传统的血液,但《冷山》的哥特意象不再局限于闹鬼庄园或畸零人种,而是呈现为更普世的精神荒原。牧师维西以圣经为名实施性暴力,猎奴者特维的犬牙项链滴落受害者的血——这些角色并非简单的恶人符号,而是战争催生的人性癌变。小说对南方神话的反思同样尖锐。艾达的父亲蒙克莱尔牧师曾坚信“奴隶制是文明的火种”,却在临终前焚烧所有藏书,留下一句“我们都被词语欺骗了”。这一场景可视为对福克纳式南方叙事的倒置:当《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昆丁沉溺于家族荣耀的幻觉,《冷山》的主人公们选择在灰烬中重生。弗雷泽的南方不再是怀旧的客体,而是通过毁灭与重建,指向一种去浪漫化的、扎根于土地的新伦理。
弗雷泽的散文风格常被比作福克纳与麦卡锡的合体,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对寂静的雕刻。他描写枪声后的林间空寂:“仿佛世界突然失聪”;刻画艾达的孤独:“寂静如此沉重,连烛光都显得吵闹”。这种以负空间营造张力的手法,使小说的暴力场景更具心理穿透力——当英曼拧断追兵的脖子时,读者听见的不是骨裂声,而是“一只夜莺在远处啼鸣”。
小说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则近乎神谕。晨雾中的冷山“如鲸脊浮出云海”,暴雨后的溪流“携带山峦的骨灰奔涌”。这些意象不仅构建了叙事的诗意节奏,更将自然提升至本体论高度:在人类互相屠戮时,山脉与河流依然遵循亘古的法则,为幸存者提供最后的避难所。
《冷山》的结局充满古希腊悲剧的宿命感。英曼历经劫难回到冷山,却在重逢的瞬间被民兵射杀;艾达怀抱他的尸体,在雪地上划出“一道血的溪流”。这一场景曾引发争议,但恰恰是这种对救赎的拒绝,使小说脱离了廉价浪漫主义的窠臼。弗雷泽似乎在追问:当整个世界陷入疯狂,个人的救赎是否可能?
答案或许藏在鲁比的故事里。这位切罗基后裔在种族清洗中失去家人,却选择以草药知识治愈邻里的疾病。她告诉艾达:“伤痛不会消失,但你可以学会与它共存。”这种“带伤生存”的哲学,与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形成微妙对话——弗雷泽并未提供超越苦难的答案,但他证明,在战争的废墟上,仍有人以记忆、劳动与爱的方式,守护着人性的火种。
近三十年过去,《冷山》的启示愈发显出其预言性,弗雷泽笔下的冷山依然矗立,并提醒我们:真正的家园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与土地、记忆、他者共处的伦理实践。这部小说最终是一曲献给所有流亡者的安魂曲——无论你是穿越战场的士兵,还是在现代性荒原中迷失的都市人,冷山的雾霭中总有一盏灯,照亮归途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