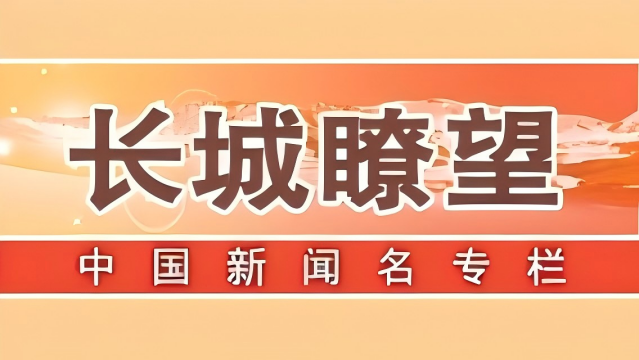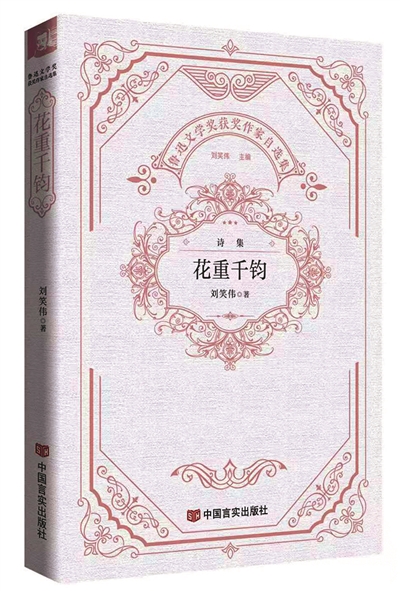
诗意描绘戍边军人的精神本色
■贾非
最近,品读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军旅诗人刘笑伟的诗歌自选集《花重千钧》(中国言实出版社),感触颇多。作为曾在火热军营摸爬滚打过的读者,我对诗集中的《昆仑》一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也试着以这首诗为个案,来评价整部诗集的艺术特色。
在笔者看来,《昆仑》这首并不太长却内蕴丰富的诗,以磅礴的气势和深邃的哲思,体现了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的鲜明特色。这首诗,以“昆仑”为意象,将自然地理的伟岸与戍边军人的精神力量融为一体,在冰与火的淬炼中,彰显出雄浑阳刚的艺术特质,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传统边塞诗歌精神的创造性传承。
《昆仑》一诗中,地理空间不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而是被诗人赋予了强烈的精神属性。开篇“一直在等待一首诗的到来/在那最初的原点,细流潺潺/拉响了高山。野鸟点燃了大漠孤烟”,将昆仑山脉的地理起源与诗歌创作的灵感源头并置,表达了自然景观与精神创造属于相同的母体。“起伏的峰峦,宛如思绪/树林和山涧是思考的产物”等诗句,将地理符号转化为哲思的具象化呈现,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双向观照。
“冻土与冰川,捧起湛蓝星空与一弯新月”,这种意象多重并置的艺术手法,进一步刻画了戍边军人的精神景观。它不是对地理环境的单纯临摹,而是将自然景观升华为精神力量载体。“不远处,雪峰林立/让人一眼经历两个季节:春日与冬天”,这既是对高原气候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戍边军人精神世界的隐喻——他们在严寒中始终守护着祖国的安宁。
第二章节中,“裸露在大地上,连绵数千里/像一部长达数万行的民族史诗/被仰望者日夜吟诵”的意象转换,在增加诗歌张力之时,使单纯的“地理空间”升华为“文化空间”。昆仑山脉被喻为“民族史诗”,其地理属性的存在已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这种转化不仅赋予自然景观历史纵深感,而且将戍边军人的个体经验纳入民族精神的集体叙事中。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展开叙事是这首诗的重要特点。“戍守久了,肌肉会像岩石/岩石也会有肌肉的质感与体温”“大声朗读历朝历代的/连绵起伏的边塞诗”……古今对话打破了线性叙事,也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激荡共振。
“一万吨雷声压进胸膛的力量”,在笔者看来这一夸张的修辞,恰是现代军人精神能量与古代边塞诗雄浑气象相联结的展现。这种力量是惊人的,让人不禁想到当年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在扉页郑重写下“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的惊叹与赞美。随之,“把一种信念托举到/天空和太阳之上的力量”,诗作赞美信仰与信念的力量,也完成了对传统边塞诗歌中家国情怀的升华。
《昆仑》一诗的语言,展现出强烈的探索性与创造性。“野鸟点燃了大漠孤烟”“冰层破裂,山泉喷涌的意象/在蓝空中,形成一把把冰刀”……这种通感手法的运用生动展现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同时,诗人通过“虚无缥缈间,满头白发的布喀达坂峰/让时间渐渐有了怀念的意义”,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心灵的载体。这种时空转换的诗学策略,使诗歌获得了超越地理时空的哲学深度。结尾3个章节中重复出现的“一直在等一首诗的降临”“标题是两个散发异香的汉字:昆仑”,让山脉“昆仑”与诗歌《昆仑》,相互交融。这种颇具匠心的结构安排,也体现了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的追求与功底。
在语感节奏上,全诗呈现出“舒缓—激越—凝定”的三重变奏。开篇中的“细流潺潺”与结尾的“异香汉字”形成首尾呼应的宁静意象,中间章节的“一万吨雷声”则构成激昂的情感高潮。这种节奏的变化既对应着地理空间的起伏,也使诗歌获得了交响乐般的艺术效果。
《昆仑》一诗是《花重千钧》中的代表作。它展现的探索特质,既散见于诗集中的其他诗作中,也让人们看到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的努力与收获。《花重千钧》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历史传统与当代价值相融合的创作实践,给诗歌创作颇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