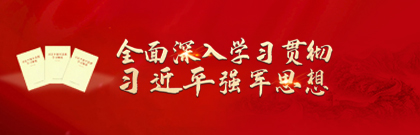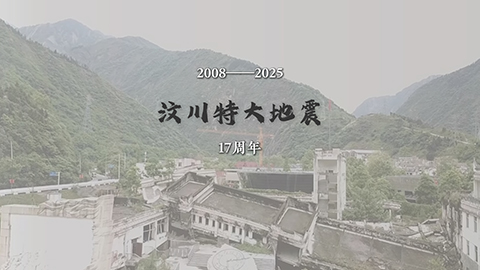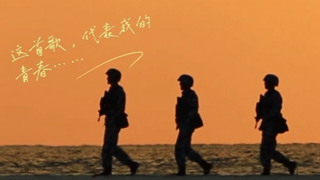新诗研究的新探索
——评李蓉《中国新诗的“身体”现代性研究》
■王泽龙
近20年来,李蓉一直致力于从身体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先后推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等3部学术专著,构成了她的身体诗学研究。
“身体”是21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在西方,身体经历了从被禁锢到被解放的历史,而身心关系则是西方身体哲学与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西方古典哲学中,“身心二元论”是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灵魂高于肉体,前者代表理性和智慧,后者代表感性与本能,因此肉体需要灵魂统领,这种精神化的哲学观念从柏拉图一直延续到了黑格尔。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反对形而上学对人类的主宰,让身体回归生命的本能。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理论进一步突出身体的价值和意义,将身心二元论改造为身心统一的一元论。西方现代身体哲学观念,确立了身体在认识世界中的优先地位,是身体而不是灵魂构建了人们对世界的原初认知,这一思想给我们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而李蓉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的。
与哲学相对应,审美领域对身体的认知也经过了从理性意识回归身体感性的过程。在李蓉看来,身体是人的物质存在,与心灵活动不可分离;现代美学与文学艺术是一门感性的美学,审美活动首先是身体性的,身体是审美的主体。身体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还有伦理、精神和创造性的一面,它们同样蕴藏在身体内部,二者是统一的。基于这样的身体诗学观,她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现场与大量的典型文本中,挖掘出文学创作中丰富的身体意识、生命烙印及其意义,探索出一条文学研究新路。
新近出版的《中国新诗的“身体”现代性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入选成果,该书认为,新诗的现代性展开中,审美的身体、历史的身体最终都呈现在语言中,现代的经验、感觉、情绪通过具有身体感的语言(节奏、语调、韵律等)来呈现。新诗作为极具形式感的文体,诗人创作的过程就是诗人的身体转换为“文本肉身”的过程,谈论新诗的身体不是简单地分析新诗如何表现身体、描摹身体,而是辨析身体在诗意的书写中是怎样被想象、被建构的,身体如何介入了新诗自身的文体构造。同时,诗人使用语言表达自我的具体处境,语言表达的不是预设的观念,而是在场的身体语言,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就是身体与意义的关联。作者进而认为,与日常语言表达相比,身体经验是更为原始的结构,只有身体的语言才能接近并表现身体感知与身体经验。身体感受、经验的模糊性与语言的诗性又是对应的。因此,身体与语言的关系成了该著考察新诗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与主要途径,为我们重新发现新诗的现代性提供了启示。
从现代性视角切入是研究新诗历史变迁的惯常方法,而以往对新诗现代性的考察,较少关心身体与新诗现代性的关联。李蓉另辟蹊径,具体探究了身体怎样参与了新诗现代化变革过程,在每一个阶段担任了怎样的角色,对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该著身体诗学阐释的重要话题。作者认为,身体现代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审美问题,也是一个包含了时代内容的新诗历史化问题。从身体意识的内涵看,对现代感性的不断发掘,对直觉、经验的重视,对真实生命体验的表达等,构成了新诗现代性的内容,它们皆随着新诗艺术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不断被深化和重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早期象征主义诗人追求感官个人化,到了20世纪40年代,纯个人的感官书写被抛弃,因为现实感的增强,身体经验中融入了感时忧国的儒家文化传统,诗歌艺术的感性经验具有了开放性,这也是新诗身体诗学所包含的中国特质。该书没有套用西方身体诗学观念,而是在新诗身体诗学观念中注意接通中国传统诗学。作者认为,古代诗歌作为一种韵的艺术,诗歌的押韵、节奏、句式、语调都关联着身体的变化,身体的众多神经都能应和节奏的打击、韵律的回环、语调的起伏。这样一种诗歌文体的身体性特征在新诗的实践经验中依然存在并不断发生着变化。
中国新诗中包含着丰富且尚未被充分关注的身体问题,新诗身体诗学作为一个理论话题与创作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