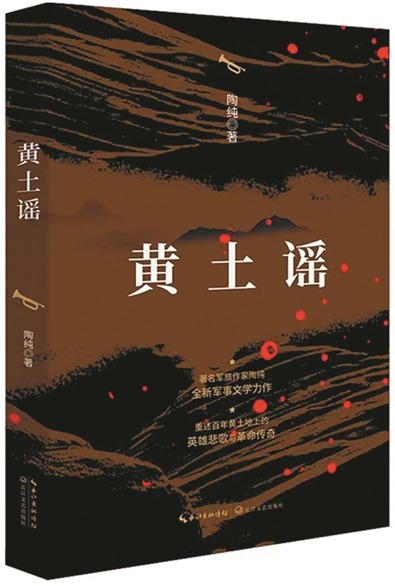
烽火、黄土地与平民故事
■曹芳
在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如何既真实再现战争,又深入挖掘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所展现出的精神力量,始终是作家所面临的挑战。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黄土谣》,是军旅作家陶纯的一部用心之作。
这部作品共收录了《黄土谣》《暗香》《生灵之美》等篇目,延续了陶纯“致力于寻找‘既吸引人又富有深意’的故事”的创作理念。他将目光聚焦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平民英雄,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历史考证,不仅重现了战争的残酷与复杂,更塑造了众多的平民英雄形象。
因此,“平民史诗”是《黄土谣》小说集最显著的特点。它摒弃了对“大英雄”的传统塑造模式,转而关注那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普通人。那一张张面孔,有血有肉、充满个性,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触动读者的心灵——他们在面对战争的残酷与生活的艰辛时,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以及对于理想与信念的坚定追求。
譬如,小说集的同名篇章《黄土谣》,以劳动模范赵有良的一生为叙事主线,描绘了革命战争年代一位农民如何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走上革命道路。赵有良出身寒微,长年挣扎于饥饿与贫困中。然而,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土改政策为他带来了转机。分得土地后,他开垦荒地、精耕细作,最终被选为边区劳动模范。他的儿子在山西长治抗日战场阵亡,女儿牺牲于兰州战役,妻子也在动荡中离世。他并未沉浸于悲情,而是通过组织支前队伍、捐献全部存粮甚至牵走自家黄牛支援前线,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又如,地主霍起原本与赵有良站在对立面。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的大儿子霍明在战场上被敌杀害,二儿子霍亮在青化砭战役中阵亡,霍起自己也在赵有良的感化下,打开粮仓支援西北野战军。作者以细腻的白描手法,描述了这个地主前后态度的转变,进一步丰富了书中的人物群像。赵有良与霍起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更是那个时代万千民众家国情怀的缩影。
在文学创作中,人物的塑造离不开巧妙的叙事。作为军事题材小说,《黄土谣》小说集的叙事风格兼具历史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作者通过大量细节考证与地域文化描摹,并充分运用地域方言与民俗意象,如陕北的信天游、黄土窑洞、劳动号子等,艺术再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边区的社会图景。同时,书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没有宏大的战争全景,而是通过“黄泥、污黑的硝烟和片片血迹糊在身上”“班长上半身密布着窟窿眼,很像碑石上刻着的红色铭文”等细节,更加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场景,让读者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以及在抗战中普通人的信仰与坚守。
在叙事语言上,作者将平实的语言风格贯穿作品始终。这种落笔方式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书中的人物鲜活立体。例如,当赵有良与邻里谈论农事、家长里短时,所用的都是最朴素直白的话语,像“老哥!干的(得)咋样了?歇会儿吧”“贺书记,额不想当劳模咧!额只想种好地,当个好老百姓”。这些日常化的对话,让读者能真切感受到人物之间质朴的关系,也凸显出他们作为普通农民的身份特征。
在刻画生活场景时,作品使用“盛粮食的瓮都见底了,无粮可卖”“上身穿着打了一摞补丁的黑夹衣,下身着灰色长裤,也满是补丁”等描述。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不仅勾勒出了当时生活的艰辛,更凸显了人物内心的坚韧与不屈。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眼神中闪烁的是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是对胜利的无限渴望。这种在困苦中依然保持高昂斗志的精神风貌,让人深感敬佩。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描绘,读者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亲眼见证那段峥嵘岁月,感受到那份深沉而炽热的爱国情怀。
《黄土谣》小说集的多重叙事视角也让人印象深刻——既有赵有良的农民视角,也有陶校长的知识分子视角,更有在《生灵之美》中以一头名为“长路”的小毛驴的动物视角。这种多重视角不仅打破了单一叙事的局限性,更在拼图式的故事中,多视角刻画了历史的立体面貌。
赵有良的农民视角既保留了传统农耕文明的韧性,又在革命浪潮中孕育出新的政治意识。他从个体劳动者到革命参与者的转变过程,展现了农民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发现自身价值,并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革命的意义。
陶校长原本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却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投笔从戎”,组织起一支“钢枪加鸟枪”的民间武装力量。这一选择既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打破了传统文人“坐而论道”的刻板印象。陶校长的形象因此变得更加立体而生动,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
小毛驴“长路”的动物视角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长路”的动物本能与人类情感交织共生,形成双重叙事动力。它因主人留根的抚触建立情感联结,在战场重逢时以脖颈蹭舐表达关怀。在后来的斗争中,它与主人并肩战斗,共同抵御侵略者,这恰是文本以动物视角刻画历史情境的精妙之处。
《黄土谣》小说集是一部充满痛感与力量的作品。它凝视战争的残酷,却始终相信人性的光芒。作者以冷峻的笔调与炽热的情怀,在黄土地上树起了一座平民英雄的丰碑。这些被历史长河冲刷的人物形象,用鲜血与信仰谱写的,不仅是一曲战争的悲歌,更是一首关于民族精神的赞歌。他们的故事,正如陕北高原上倔强生长的山丹丹,在岁月的风沙中,始终绽放着灼目的鲜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