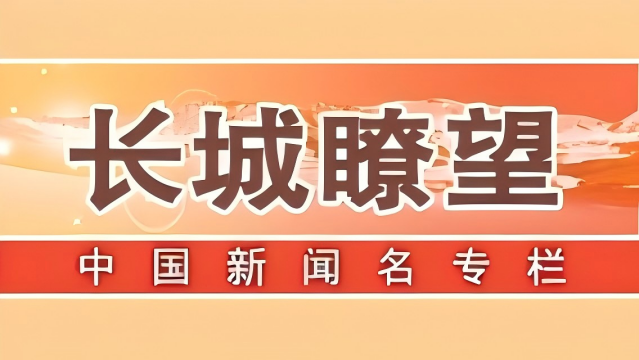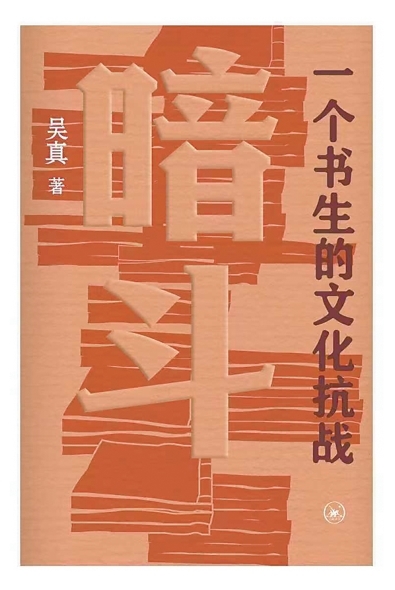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吴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7月出版
抗战“孤岛暗斗”中的书与人
■中华读书报实习记者 张钧皓 郝雪敏
“共情,要把我所感受到的书生与书籍在战争年代的共振写出来。”在谈到写作关怀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坚定地说道。
从2009年冬天在日本发现一条有关抗战遭劫图书的记载开始,已经过去了15年。15年间,吴真的关注点逐渐从搜寻中国被劫图书的踪迹,集中到郑振铎在抗战八年间的书籍事业上,试着从日藏档案、日记回忆录、题跋赠语、书店账目等多元文献中拼接出另一幅“文化抗战”的拼图。
2023年底,此前从未面世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现身上海。这本日记记录了郑振铎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筹备工作,恰恰补充了吴真过去十年间搜检史料的一个缺环,也令郑振铎在全面抗战八年之间的上海秘密工作连贯成为一条完整的时间叙事线。2025年正值抗战胜利80周年,吴真新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于7月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打通书籍史与抗战史,再现了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以及“开明文人圈”等留守上海的文化志士,与多方势力争夺民族文献的历史场景。15年的积累和念念不忘,终于迎来初步成果。为此,本报就本书的内容和写作过程,对吴真进行了采访。
“这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吴真并没有显得如释重负。“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只是抗战时期遭受劫难的众多民间私家藏书中比较幸运的一批。”选择从郑振铎入手调查中国战时被劫书籍,既是因为这批图书具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和保存,也是希望借着郑振铎的事迹引起公众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但是沉默的大多数书籍很难讲清楚,所以我先从容易的做起。我后面的工作是要继续追查失踪的书籍。”
然而这并非吴真的主业。吴真的学术主业是古代戏曲俗文学研究,追查失踪书籍主要是出于身为读书人对书籍命运的关注,以及对郑振铎这位俗文学“祖师爷”的共情。曾有人调侃在如今卷无可卷的学术界,这种不务正业令人难以理解,就连吴真本人也曾陷入过精神内耗。或许是受到郑振铎天真、无所顾忌的书生心气隐隐感召,吴真坚持了下来。“我现在的年纪正好是郑振铎当年在上海抢救书籍的年纪,所以我常常在想,郑振铎在那样的历史暗夜中还能够那么一往无前,同为中年的我,处在比他好得多的时代里,更有条件做一些事情。”在说起这位祖师爷的“可爱”之处时,吴真仿佛共享了那一分坦荡,“我只想不要辜负这么多年来搜集的文献资料,不要辜负西谛先生通过书籍给我们传达的心意。”
在这个时代,“讲好一个人、一群书、一个时代的故事足矣”的心气,与讲好这个故事的能力同样重要。
一个人:历史迷雾中摸索人物生命轨迹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后记提到您关注“中国被劫图书”15年。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旧书业的研究,并关注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
吴真:1938年广州沦陷时,日军占领了我的母校中山大学,将其作为华南派遣军司令部。中大师生撤退时太过匆忙,大部分藏书未及运出,落入日军手中。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大复校时,发现约有七八十万册藏书遗失,这批图书的去向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偶然读到日军随军记者内藤英雄的《广东战后报告》,得知日军曾派遣专门的图书整理小组前往广州处置中大藏书。于是我开始留心搜集日本方面的线索,如日本军方档案,以及随军记者、学者、士兵的回忆录。在这期间,我的搜索范围不断扩大,视野也从中大被劫图书扩大至中国各大公立图书馆的被劫图书。为此我跑遍了可能存有被劫图书的机构,比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以及此前较少为国内学者关注的亚细亚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追查被劫图书并不是我的研究本职,我只能用业余时间缓慢推进这项工作。手头的资料逐渐积累,众多个案也慢慢浮现并清晰起来,郑振铎在上海抢救的近六万册书籍则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是抗战时期为书籍留下最多文字记载的历史见证人,不仅亲历了战时图书遭劫、战后图书追索的过程,而且留下了将近六年的日记和大量的纪实文章。而且他有个习惯就是,但凡购入一种书籍,都会写下题跋,详细记录其来源、获得渠道,以及收集过程中的艰辛。1939年底他开始帮重庆的中央图书馆收购书籍,牵头组建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制定了严密的搜书细则,所以这两年之间郑振铎也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报告、往来信件和账目支票。我相信没有一位上海文人留下的书籍史料,在丰富性和多维性上能超越郑振铎。因此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可以得心应手地择取素材、还原历史情景、搭建因果链条。巧妇幸而得米,所以能炒出一盘好菜,我很幸运遇到郑振铎这个研究对象。
郑振铎保存文献事业的重要性,其实并没有被很好地阐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定程度上也与他1958年因公殉职以及抗战胜利后他对此事较为低调有关。郑振铎在1945年底《大公报》上连载其记录抢救文献的《求书日录》,但此文后来未再连缀出版,直到1983年《西谛书话》才首次收入此文。就连其好友叶圣陶,当年在抗战时经常埋怨郑振铎为何不撤退到内地,他也是四十多年之后看到了《西谛书话》,才知道郑振铎留守上海秘密抢救工作的实情。后来陈福康、苏精、沈津等等学者接触到“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档案,开始写文章披露,才使得郑振铎的“文化抗战”有了一定知名度。
而从总体来说,抗战时期民族文献与文化保存的话题,也是近几年学界讨论文化抗战时才比较多地被提及。历史学界主要从政治、军方行为等角度,关注书籍遭劫这个事情的整体及其意义。我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更为关注书籍与人的命运在抗战中的共振。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每一次搜购、转运对书籍的影响,尤其是书籍最后的下落,这是我研究的起点,也是终点。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郑振铎是否具有某种特质与品格,支持他在战时艰苦凶险的环境中完成文献抢救的事业?
吴真:首先,我举得郑振铎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与人为善,尤其体现在他与书商群体的交往中,他平等地对待这些商人,让他们有微小利润可赚,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积极配合国家收书。战后郑振铎参与了对战时附逆者的清算,他主张对待那些担任汪伪及日军伪职的汉奸、“落水者”一定要追查到底,但是对于那些并未“变节”、而只是态度上暧昧的普通人,他还是有所区别对待的。比如他战后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刻意回避了旧书买卖中间人陈乃乾在日本文献学期刊上抢先公布《古今杂剧》的事实。这种曲笔,不仅是因为陈乃乾与他多有合作,更是因为郑振铎心中怀有对战争中普通人艰难抉择的悲悯,他评价陈乃乾是“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陈乃乾这样的个体书商,既没有政府身份支持,也未当过大学教授,在沦陷区的生存艰难可想而知。郑振铎能够理解留守上海的普通人战时维持生计的不易,因此只要不损害基本立场,他就会让书商有钱可赚,有利可沾。这种处事智慧,我认为是他在战时复杂艰苦环境中能完成这项事业的重要条件。
其次,我在本书中尤其想要突出的是郑振铎身上属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斗争精神,这也是我以“暗斗”为题的原因。所谓“亡人国者必先亡其史”,郑振铎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并且积极对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文化侵略。早年郑振铎的搜集兴趣主要是俗文学文献,而到抗战时期,他转而注重收集地方史志和地理这两类图书。他超越了一个研究者的个人视野,站在国家立场去抢救文献。所以我们会发现,郑振铎抢救图书的目的性、斗争性很强。比如嘉业堂这一批藏书,他与多方势力明争暗斗,千方百计一定要争取使其为国家所有。而且他没有去洽购那些传统藏书家偏爱的宋元版书籍,反而积极搜购明版史书与文集。因为从国家立场来说,这批明版书里的地方志最为完备,属于有用且罕见的文献。郑振铎是从与日本侵略者积极争夺“历史记忆”的高度来开展抢救文献工作的,这种国家立场是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核心。
在收集材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也在与郑振铎这位先贤对话,从他的经历和话语中得到一些治愈。有几年时间,我面对越来越严苛的学术考评环境时,产生了比较大的“精神内耗”。这时候读读郑振铎的文章,从他的大格局、大情怀里,获得了很多的情感支持。郑振铎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学者,我们从1939年日记里可以看到他一边娱乐(一年看了近二百场电影),一边写文章,一边还能为国家谋划很多事业。1939年底,面对重庆当局提出的暂时无法拨付经费支持但可以请上海的郑振铎先行动的“空头支票”,他不去计较,立马着手收购书籍。这种行动力,有赖于他的天真与纯粹,可能正是这样的气魄,才支撑其闯出一片天地。其实他当时在民国学界的学术评价不是很高,一是因为他的观点很大胆,二是因为他做事大开大合、不顾细节。但是别人怎么看,从不会造成他的精神内耗,他照样一往无前。这些品质决定了他在八年的历史暗夜中,脱离了按部就班的学者轨道,做成许多了不起的“事功”。
一群书:“人事”与“书事”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书中,书商群体是郑振铎抢救文献时紧密依靠的伙伴和战友。您为何会关注这一群体?您如何评价近代的书商群体和旧书业?
吴真:我一直以来都比较关注旧书业的行业生态问题,因为我的主业是研究民间戏曲和俗文化,为此经常需要到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在此期间旧书业逐渐进入了我的视野。利用田野调查了解到的商业运作细节,帮助我从文献里“还原”具体生动的历史情境。例如,按照清代和民国的旧书业惯例,学者买书不需要付现金,而是采用赊账的方式。到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书店的伙计就会拿着账单上门结账。这是一种旧中国通行的商业法则,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如果要理解和复原历史上的文人生活,了解这些行业生态是必须的。
我这本书的写作,极大得益于对旧书行业生态知识的积累。比如说1941年,郑振铎在重庆当局没有给予帮助的情况下,在两个多月内把将近3万册书秘密运到香港。以往学界指出唐弢利用邮局工作的便利,帮助文献保存同志会避开检查邮寄信件,打通书籍转运的联络网。但是要将数目如此庞大的书籍妥善运出,显然还有更大的团队和人际关系网络在支持。我从郑振铎与书商的频密联系入手,发现了中国书店在书籍转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振铎与中国书店长期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信任。中国书店是外地书商到上海搜书的集散地和中转站,还为外埠客人提供订购书籍邮寄上门的服务,每天发送的书籍邮包多至千余包。中国书店的书商杨金华等人于是将文献保存同志会搜集的古籍混入发往各地的海量包裹中,终于顺利瞒天过海,邮抵香港。在日伪封锁严密、国民政府态度消极的情况下,郑振铎正是依靠旧书业的商业网络完成了这一转运壮举。
了解旧书商的行业生态,最重要的就是理清这套文化商业网络。我把旧书商称为“横通者”,此概念由清代大儒章学诚最早提出。他认为在藏书家和学者之间,需要有一批促进书籍流通的书商。这些书商具备很高的专业水平,能够鉴赏、鉴别古籍的版本。从晚明至清代,正是这一群体的活跃,促进了整个清代的书籍文化从刊刻出版到流通阅读的大发展。这些“横通者”的存在,使得以书籍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得以成立,并且愈发扩大。
旧书商对于民国学术的促进功能更加显著。古代学者找一本较为罕见的书籍,可能就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这种情况到了民国大为改观,比如一些学者的日记里提到,他们为写文章准备材料时,先去旧书店列出一张访求书单,一段时间过后,店伙就会把书目上的书送至家中。所以说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兴起之前,旧书业为学者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料,这是民国时期学术大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了解近现代学术日常生活的重要窗口。

▲吴真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从书籍史的角度提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书籍的苦难,也是全人类的苦难。”郑振铎的个案如何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整体关怀联系起来?
吴真:上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搜集的图书,是中国被劫图书中最幸运的一批,因为这批书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大部分中国图书被日军劫运到日本后,先从陆军省转给文部省,文部省将其分割后再分给各个单位,致使这些图书散失各处。而且相当一部分接收图书的并不是专业研究机构,他们只保留那些对他们有用的资料,而余下的书籍可能就处理掉了。但是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这批图书在香港大学被掠走的时候,共有111箱,被日军23军从香港整批打包到日本,又整批发给了帝国图书馆,由文献专家长泽规矩也专门整理。1946年,中国代表团在追索的时候出具了郑振铎存留的完整书目,可以跟图书馆里的古籍一一对应,这批书得以完璧归赵。
但是还有大量被分割到日本各地的中国被劫书籍没有这么幸运,它们在日本战败后失去了踪迹。我后面的工作是要继续追查这些“失踪者”,因为抗战书厄不只是一批图书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一群书的问题。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这批图书相对来说,转运经过各个站点的信息清晰明了,公众关注度也比较高。其余的被劫图书,搜集、整理、研究起来可能更困难。
一个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它的文明和文化也必然在遭受破坏。如果我们把书籍当作是文明的一个象征,我们会发现每个国家经历战争时,书籍也在经历磨难。西方书籍史对此开展过研究,不过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专题化。我希望《暗斗》这本书,能够把中国书籍在战争中的历难史,描绘得更加细节、具体。西方的书籍历难史跟中国不太一样,因为西方很多图书是收藏在教堂里的,且多为宗教书籍;而在中国的传统中,书厄这个概念一般指官方藏书。但事实上就中国抗战而言,受难的书籍从内容来看多为传统经史文学典籍,这与以宗教为底色的西方文化有异。而且中国从宋代之后,民间藏书楼文化盛行,抗战时期,私人藏书楼的损失尤其巨大,因为个人在战乱时更加缺乏保护图书的能力。
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保护的并不是国家图书馆或者是某个大学图书馆,他们保护的是从沦陷区的一个个家庭散落到上海的图书。我把他的工作称为“郑振铎大坝”,他把战时从各处流落到沪上、即将再次流散海外的书籍加以聚拢拦截。这个工作可以与书籍史意义上的“战争与书籍”和中国传统文献学所讲的“书厄”分别展开横向、纵向的对话,是应当被大书特书的事业。
一个时代:从个体生命中窥见历史的洪流
中华读书报:我们常说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您是否从郑振铎这样的书生身上,看到了这种觉醒的具体发生?
吴真:从郑振铎的日记和纪实文章中,确实能发现抗战时期思想转变的轨迹。他在《劫中得书记》里提到,当看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称,中国古籍源源流入美国”这条报道时,他大受刺激。他认为,如若不帮国家去做点事情,子孙后代就要到国外去看这些书了。在争夺嘉业堂藏书时,他在写给时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的信中恳切地写道:“如此批货为外人所得,诚百身莫赎之罪人也!”这种焦虑是他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族自觉,也是他全情投入抢救古籍工作的一个动因。
另外,留守上海“孤岛”给他带来了一种道德愧疚感。这种愧疚为“孤岛”文人所共有,被一次次来自他者和自己的道德拷问所强化,在郑振铎身上尤为突显。他迁往内地的朋友们,如叶圣陶、巴金等,多次责怪他的留守。这种愧疚强化了他的焦虑,最终使郑振铎自觉地承担起保全民族文献的文化责任,以“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为报效国家、实现自我的途径。
其实我们在郑振铎文献抢救和整理出版的实际工作中,也能看到其国族意识的觉醒。他在1937年后就意识到私家藏书在此动乱时代无法保存,将其全部转化为公有才更稳妥。而他为国家抢救的历史类书籍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着眼于“倭史”。他在上海秘密组织出版《玄览堂丛书》,挑选了40多种古籍进行影印,其中有七八种是“倭史”,即明清时期中国人写的日本史料。第二是偏重明代文献。他集中收购未被收录进《四库全书》的、于清朝文化剿灭中幸存下来的明人文献,并出版了《晚明史料丛刊》。这种着眼于民族国家历史记忆构建的文献搜集,是一种现代性学术的自觉。
中华读书报:您的书中有一条没有明确指出的“暗线”,即抗战中的学术新旧交替。您指出抗战时期,是中国旧书由私人家藏走向国家馆藏的关键阶段,特别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购使大量私家尽归国有。您是如何看待郑振铎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地位呢?
吴真:郑振铎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他将学术资料作为学术公器加以收集和运用的实践中。他的这种意识,并非始于抗战时期。早在《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一文中,他就提到1933年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值得被记录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有许多重大文献发现,并且这些文献在被发现后就迅速进入资料流通领域。郑振铎和那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研究者,都认为古籍应该是学术公器,发现后要共享给学界,这样才能促进学科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比如1933年,郑振铎通过向达获得了藏在苏联的孤本《刘知远诸宫调》照片副本。他如获至宝,立即写出首篇研究诸宫调的学术论文,并迅速将照片整理成文字,在其主编的《世界文库》中出版。
民国的学术转型有一个特点,即学术的竞争逐渐由资料占有权的争夺转化为对首发权的争夺,后者是现代学术的重要表现。大部分民国学者的惯例是:先占有学术资料写出一篇论文,然后再将其影印或者整理刊布,使之成为学术公器。传统的私人藏书传统是这一惯例的反面,因为私人藏书总是深藏于家中,避免文献公开。明代稀世珍本《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便是如此,收藏者丁祖荫将其束之高阁二十余年,不敢广而告之,结果直到去世,其子孙也不知其重要性,以致这套珍本流落坊间。郑振铎这批学者兼藏书家就致力于改变这一情况,他们在1938年经过争取公家购置《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后,马上联系商务印书馆,1941年将其整理出版。这个抗战时期的例子正说明郑振铎那一批学者怀着“古籍为学术公器”的大爱,去进行文献抢救和研究。
这种将私家藏书转化为公开的学术风气,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学术转型过程,郑振铎是其中一个积极的推动者。郑振铎生前收集的个人书籍,一共将近9万册,大部分保存在公共图书馆中。尽管其中被公开刊刻、出版的,只有1%不到,然而正是因为保存在公共图书馆中,它们的研究价值才逐渐被后来的学者一步步地发现。也就是说,它们完成了从私家藏书到公共藏书的转变,进入公众视野,服务于现代学术,这正是郑振铎生前孜孜不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