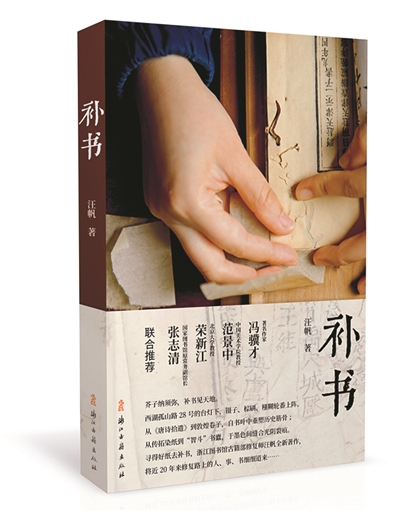
漫谈古籍修复
■杜伟生
作为一位在古籍修复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修复师,看到汪帆这本《补书》(浙江古籍出版社),内心感触良多。
古籍修复这门技艺,看似简单,实则也有复杂之处。其流程主要包括分解、修补、压平和复原几个基本步骤。然而,每一步骤中的方法技巧,需要通过经年累月的实践去领悟。例如,将一本书“分解”成单页,并非易事。书页可能因虫蛀而粘连严重,甚至面目全非,如“打井”般自上而下蛀穿,或像“挖巷道”般在书页内转圈啃噬;也可能被霉菌侵蚀得脆弱不堪。针对这些问题,修复方法有干揭、湿揭,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蒸揭”——这不是蒸馒头,而是利用蒸汽逐步润透,再小心翼翼地揭开,对分寸的把握至关重要。对于粘连特别严重的情况,还需采用“粘接”法,借助浆糊的力量进行分离。这些都属于修复前的“诊断”环节。
进入“修补”环节,选纸用纸便显得尤为重要。许多人误以为溜口纸(粘贴断裂的书口和撕裂处的纸)越薄越好,实则不然。面对残缺破洞,若纸太薄太软,修补后折页处容易隆起不平。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纤维较长的纸张,如桑皮纸,用于溜口效果更佳,因其伸缩性小,能保持平整。至于压平方法,传统采用“拱桥法”垫纸倒书,虽费时费力,却有其独特道理。如今,年轻人多青睐从日本传入的“板压法”,效率高但占用空间。技术本身在不断演进,我们如今所用的,已是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手段的“现代技术”。
不过,最后的“复原”装帧环节,则需要尊重古法,从线眼的数量到黄檗染纸、瓷青纸等防虫染色工艺,都是力求还原其本真面貌。因此,掌握基础操作或许几个月就行,但要将技艺做到精湛,确实需要倾注一生的心血。
汪帆的这部《补书》,与我当年所撰写的作品有着显著差异。我们这一代修复师,由于早年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写作时首要目标是准确传达技术动作和流程,确保内容清晰易懂,因此语言风格难免显得直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有些枯燥。而汪帆这本书,语言活泼生动,充满了她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这种表达方式更能吸引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去了解、亲近古籍修复。
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欣喜之余,我也深感古籍修复在理论建设上的迫切与不足。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存在局限,很难去系统地构建理论体系。目前,中国古籍修复在材料史、技术史的梳理方面几乎是空白,能初步整理清楚历代装帧形式的演变已属不易。更深层的,比如修复伦理学的构建,更是亟待开展的工作。什么是修复中的“度”?如何平衡干预与保存?修复行为本身的价值判断依据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深入探讨。一些同行在教学中已引入了伦理学,我们迫切需要迎头赶上。填补这些理论空白,我们这些老修复师力有不逮,这需要像汪帆这样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年轻修复师,与高校、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来完成。希望汪帆和她的同辈们能继续努力,在这方面做出更多探索。
最后,关于修复工作的节奏问题,我想说点实际的看法。我年轻时经历过严格的定额管理时代,要求“一天一册”。这在今天看来近乎苛刻。随着保护理念的深入,修复工作确实应该更注重质量,给修复师更从容的时间去精雕细琢,追求“做到他认为好为止”的理想状态。实现这种状态,关键在于在合理的制度规范与修复师的专业自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证修复质量,又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保护作用。这需要我们整个行业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补书》的出版,是古籍修复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年轻一代古籍修复师用新的语言讲述古老技艺的活力,也承载着我们这些老修复师对技艺传承深化的期望。路还很长,但看到像汪帆这样的后来者,我对这门古老手艺的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