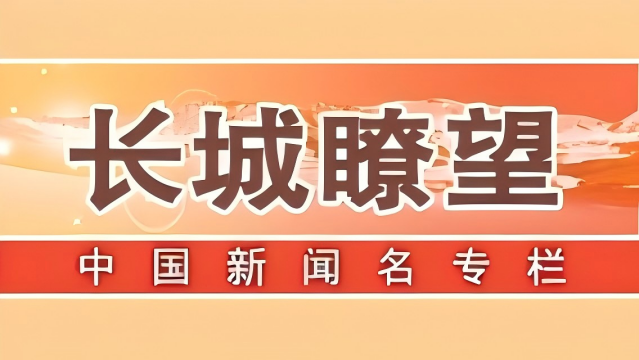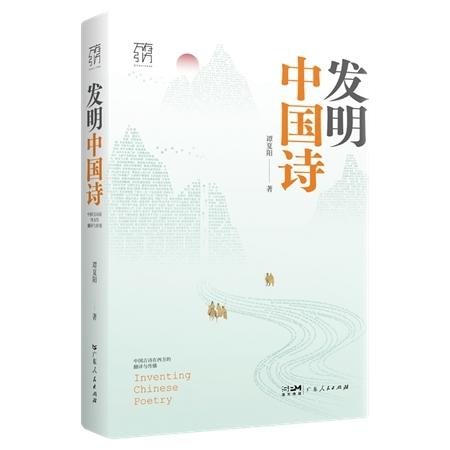
▲《发明中国诗》书封。 作者供图
当李白“抵达”旧金山,中国古诗被重新“发明”
■谭夏阳
1998年,一支德国交响乐团来华演出,演奏的曲目是90年前马勒创作的《大地之歌》,乐曲中的歌词则来自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诗。由于文化时空的辗转腾挪,有部分古诗歌词竟然找不到对应的原诗了。
这桩有趣的公案,引起中国文化界广泛的关注:一个世纪前,唐诗是如何传播到国外,并让国外艺术家产生共鸣,进而影响其创作的?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各方人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推断,甚至在报纸上展开热烈的讨论,一时间“烽烟四起”,热闹非凡。
我也被这个唐诗的故事所吸引,沉浸在一种奇妙的文化碰撞中,久久不能忘怀。后来我成为一个诗人,写现代诗,常常关注外国的诗歌动态,也关注“中国古诗在海外”论题,并逐渐读到一些与“中国诗”相关的文章。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相当迷恋一首中国古诗在国外的传播历程——它翻译得如何?有没有变形?读到它的外国读者会有怎样的感受?更深入一点,它对该国的文学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诸如此类。
已经出版的《李白来到旧金山》和《发明中国诗》,我都讨论了中国诗歌在海外传播的论题,然而两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李白来到旧金山》主要描述了中国9位古典诗人在海外重新构建自己诗人形象的过程;而《发明中国诗》则着重探讨中国诗歌在西方的接受与影响,分析其如何被翻译、解读并融入当地文化,展现出中国诗歌的跨文化魅力。
中国古典诗人在被译介到西方的过程中,其实面临了种种问题,包括误读、误解、正名,以及受人追捧的整个经历。这个历程异常艰辛、困难重重,每位诗人在西方语境中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但最终,他们都在国外读者面前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形象。
比如李白,刚开始“抵达”西方时,因为“酒鬼”的形象被人诟病,当中充满了种种误解。他是经过更多译介的印证与时间的洗礼,才慢慢恢复到国内“诗仙”的地位的。
第一批在国外建立自己诗人形象的,是李白、白居易、陶潜等人。这批诗人有一个特点,他们的诗作都很清新、自然、易懂,没有太多典故,翻译过去容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第二批才是王维、寒山、杜甫等人。
此时,美国诗坛通过大量的译介和研究,逐渐从李白、白居易、陶潜等诗人转向了王维和寒山,这表明美国诗人开始走向成熟,由中国诗的外在形式转向内在精神。与此同时,美国诗人还通过雷克斯洛斯(中文名“王红公”)对杜甫的翻译,辨认出杜甫的伟大来,这当然比认识到李白的天才与浪漫更为深刻。
以上是《李白来到旧金山》的内容,《发明中国诗》则从诗歌文本出发进行深入探讨。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进入蓬勃的发展期,其间出版了一系列广受英文读者欢迎的译本,如翟理斯的《古今诗选》《中国文学史》、克莱默·宾的《玉琵琶》《花灯盛宴》、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英译唐诗选续集》等。这些译本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为推动中国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中国诗译作皆以格律诗体来翻译,讲究节奏,力求押韵,因而也不免堆砌辞藻,带有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情趣。
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翟理斯为代表的传统汉学家和以韦利为代表的现代汉学家进行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在这场关于翻译方法的辩论中,虽然传统汉学家挟他们早前建立的权威稍稍占了上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逐渐认同现代汉学家的观点:摒弃韵体格律,采用自由诗体来翻译中国诗才是正途。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也是英语诗歌的一次现代性革命。
这次论战之后,原先大行其道的老派译本慢慢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在时间淘洗中慢慢站稳脚跟、并最终成为经典的,是这些译本:庞德的《神州集》、韦利的《中国诗170首》、宾纳的《群玉山头》以及洛威尔的《松花笺》。
此外,在那个年代,国外中文专业的高校学生几乎人手配备一部《葵晔集》,这是一本中国历代诗词选集,翻译质量经受住了时间检验。而在各大诗人的案头或他们的文字当中,常常出现《白驹集》的身影,这本薄薄的汉诗译集让诗人们爱不释手,常读常新,并成为激发他们创作的源泉。
中国诗在西方译介与传播的过程中,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西方诗歌的发展。两次美国现代诗运动,都与中国诗有着莫大关系。美国现代诗运动,在文学史上称作“美国诗歌复兴运动”。这个运动促使美国诗歌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化,最终摆脱“英国附庸”,创造出独具美国本土化的全新诗歌。
第一次美国现代诗运动发生在20世纪10至20年代,以意象派为主。意象派强调使用鲜明的意象来表现诗意,主张把诗人的感触和情绪全部隐藏到具体的意象背后,即只描写具体的对象,而不去探寻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与阐发的社会意义。
事实上,意象派探索的是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运用问题,而中国古典诗歌,正好是这一形象思维的实践成果,与意象派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中国诗在这一时期被大力推崇和大量仿写,影响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二次美国现代诗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史称“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先后产生了垮掉派和深度意象派等诗歌流派,和中国诗同样有着很深的渊源。本次“中国式”诗人更加倾心于中国诗所蕴含的“禅”与“道”。也就是说,他们更希望深入中国美学的核心,以期找到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这次中国诗的作用持续时间更长,也更为广泛,还有许多不是上述几个流派的诗人亦深受中国诗的影响。
至此,我们发现,当汉语诗歌通过翻译进入其他语系,就会自然而然地与之发生反应,最终成为其文学传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诗人艾略特评价庞德的那句名言:“庞德,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它道出了一个这样的真相:中国诗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国诗被翻译的过程,也是被重新“发明”的过程。
(作者系诗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