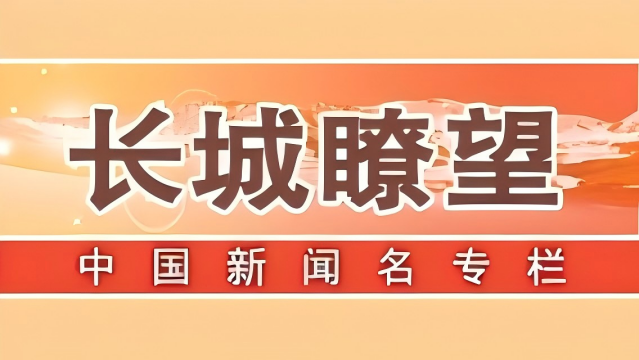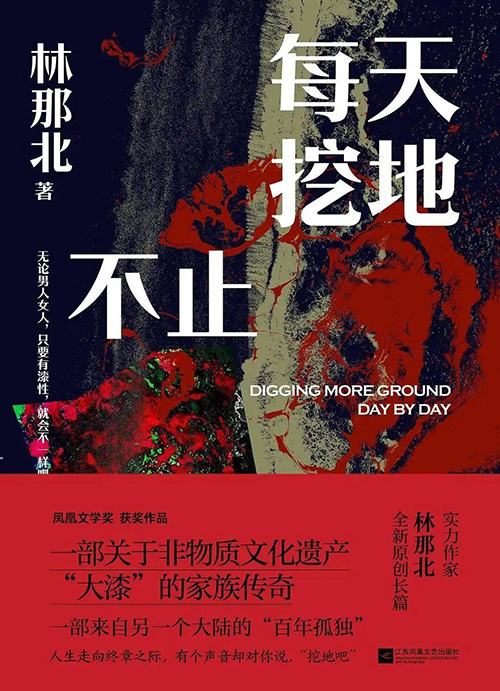
从故乡走向远方
■林那北
从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向南走,过了闽江,再过了闽江支流乌龙江,以及乌龙江支流淘江,行车记录仪显示只需要15.4公里,就可以抵达一个叫尚干的地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明白“尚”和“干”两个普通字所组成的这个词,其实它们是官名,全称为“尚书省干办官”。古代中央政府中,尚书省是最高机构,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执行国家各项政令。干办官位不大,这个只在宋朝出现过的官职,甚至史书上都很难查到它具体明确的界定,只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官员而已,核心职责是收发、登记、抄写文书,确保政令在尚书省与六部间流转。
至少我从未听说过,还有什么地方选择将官名作为地名。尚干却是直截了当的,它把一个并不太显赫的职位明晃晃戴到自己头上,以此致敬一个叫林津龙的祖辈。
南宋理宗宝祐四年,即公元1256年,28岁的林津龙高中进士。此后他并不得志,与同榜的文天祥、陆秀夫等人相比,始终未被政治聚光灯笼罩过,也没太多荡气回肠的事迹值得称道,虽敢言勇谏,且清廉刚直,也无非历任过国子监丞、监察御史、尚书省干办等职。1275年,南宋气数将尽,他不想再仕元朝,便退隐老家——乌龙江边的枕峰村。但那里有官道经过,嘈杂的车来人往不利于子孙安静读书,于是便迁居淘江畔的塔林村。两百多年后,林氏已在这里衍成望族。明成化戊戌年,即1478年,中进士后双双在京为官的林氏二十世孙林世调、林世南兄弟一起上奏明宪宗,请求准许将林津龙曾经的官名作为乡名,获准,于是塔林被改为尚干。
这里其实是个半岛,一面靠山,三面环水,螺江、峡江、淘江、五通江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岛洲有十八个之多。出门就是水,所以游泳通常是这里男女学会的第一个人生技能。溺亡虽是大悲,在这里却是年年上演的剧情。
我父亲就是尚干镇人,曾任县体委主任,他唯一会的体育项目只有游泳,姿势一般,但耐力惊人。小时候我目睹过他泡在闽江急流中长久击浪前行,被周围人赞扬,他大眼一瞪,一脸都是小菜一碟的得意。不知道他算林津龙的第几世孙。他刚出生九个月零八日,他的父亲就因伤寒病逝,年轻的寡母不肯改嫁,绝食六天六夜后,抱着他逃回邻村的娘家,靠替人做针线活把他养大,送进城里的学堂,至死都没有重踏旧地。但很奇怪,我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讲述这里的一切:水的丰沛、粮食的丰盛、小吃的多样、女人的好看、男人的暴脾气……
许多年前,我以短文《远远的亲人》,怀想一个叫林狮狮的尚干人。清光绪十年,法国军舰入侵马江,清政府却严令福建水师不许开炮击退,“动则斩”,以至于这年的8月23日法军趁着退潮时突然开火。仅仅半小时,猝不及防的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十几艘战舰被击毁,七百多将士葬身水下。受雇在附近蚬场看守蚬子的林狮狮气不过,连夜带着十几位尚干男子不顾一切驾起小盐船,以土炮轰击法舰。这当然是以卵击石,他们很快被回击,全部命丧马江。
还有一个尚干男人,我奶奶也两眼发亮地反复提起,就是林祥谦。作为汉口机务厂工人,林祥谦是1912年20岁时才离开家乡尚干去武汉的,10年后成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第二年春京汉铁路全线大罢工爆发,林祥谦被选为罢工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与军阀吴佩孚的手下正面交锋,被俘,绑在火车站台前的电线杆上。军阀先以扣工资、杀家人威胁他下令复工,他拒绝,留下“头可断、血可流,工是不能复”的豪言,直至命断。那天是1923年2月7日,这一事件史称“二七惨案”。关于他被杀过程,网上查到的很简略,说他身中七刀,最终枭首而亡。尚干人流传的则详细些:那七刀先是砍下右臂,再左臂,最后是脑袋,后颈仅剩薄薄的一层皮与身体相连。当时他年仅31岁,留下两岁的女儿和尚在腹中的儿子。
很好奇,林祥谦会武功吗?据说清代时这里的男人习武成风,刀枪棍棒,终日呼呼有声。这里有几位考中武进士,中武举人的则有二十多人。“拳头大”是一个可以炫耀的本事,意味着功夫好,一身结实的腱子肉,既能不畏强敌,也可以威震四邻。在福州地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尚干外甥”这个说法,它代表着此人不可欺、休想辱,因为他的背后有着一群强大的尚干舅舅,他们随时可能亮出拳头与你一决高低。一直以貌美被十里八乡广泛称道的尚干女人,因此就必须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氛围里,永远替夫婿、子孙担惊受怕,又忍不住一次次为他们骄傲自豪。某些时候,她们眼中的火暴脾气,是否不知不觉就与“血性”“阳刚”画上等号了呢?硬,这个字常常是尚干人的最高赞美——骨头硬,讲义气,爱憎分明,绝不苟且,路见不平就怒发冲冠,甚至不惜以命相搏。有时候我不免困惑,这个被一道道柔软水流密集包裹的小镇,为什么竟能如此血性豪情地鲜明凸显在这块平和的土地上?

▲福州市闽侯县尚干镇淘江龙舟会。 光明图片/IC PHOTO
这么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的性情中人聚集着,又遍地都是流淌不息的江水,那么最能展示原始力量与激情的龙舟赛,就顺理成章地登场了。“老婆没第一,龙舟没第二。”这句话生动体现了尚干男人对龙舟不可替代的炽热钟情。每年端午节前后,很多在外谋生的青壮汉子甚至会不由分说放下手中的生意赶回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否坐上舟,坐到舟上哪个位置,是关乎家族荣耀和自己脸面的大事。四通八达的河面,那些天全都被一条条龙舟充填,鼎盛时有两百多艘。细长的舟身迅猛欢快地犁开波涛,喧嚣的锣鼓声和冲天的呐喊声震耳欲聋。整个镇都在沸腾,女人、老人、小孩也齐聚江河边两眼发亮地翘首,跟着锣鼓声竭力喊到嗓子发哑。1988年福建省举办首届龙舟赛,尚干派出男女各一队参加,竟双双获冠军。
2003年我在中篇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里,写了一个性格刚烈执拗的尚干女子,她叫奈月,从小就痴情于同村相貌干净的李富贵,李富贵却只爱外乡女子古菜花。某天古菜花突然跟着来家里做家具的木匠私奔,李富贵外出寻觅了一年无果,终于疲惫不堪回到老家,决定接受苦苦等待的奈月。漫长的岁月里奈月坚持不婚不嫁,无怨无悔支持着李富贵,父亲要砍李富贵家的树,她提着斧头挡在前面,扬言敢砍树她就敢砍自己的胳膊。可当李富贵终于接纳她,她却看到脱掉衣裳的李富贵,其实也不过是庸常的肉身,多年的幻觉顿时破碎,于是第二天一早就掉头而去,开始帮着李富贵寻找妻子古菜花。
2013年我在另一部中篇小说《龙舟》里写了一个从小跟爷爷习武,然后进城当保安的尚干男人,叫万炳。他应聘时,凭着单手捏碎啤酒杯被物业公司录取。此时物业正与业主关系紧张,业主以拒交物业费进行抵抗。物业主任让万炳在小区表演武术试图震慑众人,又让万炳不合常规地与各住户斗智斗勇,却一次次事与愿违。但在交锋的过程中,万炳以本真的诚实、正直、讲义气渐渐获得大家认可,双方的对抗不知不觉间开始松动。终于,一个契机出现,市里为了增进邻里和睦将举办一场小区龙舟赛。可这个小区却没有经费租龙舟。此时擅长拳术和驾驶龙舟的万炳爷爷,将龙舟从尚干驶来,他年逾花甲,但一身结实的肌肉仍昭示着力量。小区里四分五裂的业主第一次与物业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去争取一场胜利。
据说正是为了将儒雅的文风渗进彪悍民风中,清光绪年间,太子太傅陈宝琛在尚干倡建书院。陈宝琛是一江之隔的螺洲人,他的老家与尚干屡有龙舟赛,因赛事曾引发过的惨烈械斗显然也惊心动魄地留在他记忆里。尚干曾有座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即公元1447年的淘江书院,当初是本族林氏子弟读书场所,员生大约二三十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岁月侵蚀,早已人去楼空了。于是在其旧址上,壮观的陶南书院被拓建出来了——筑起高墙,建起房屋,飞檐层层叠叠,门窗连绵不绝,面积多达两三千平方米,可容一百多位书生,而书院的牌匾也由陈宝琛亲自撰写。

▲陶南书院门匾。 资料图片
从那时起,陶南书院成为这一带最高学府,读书声持续不断。1933年尚干人林森回乡祭祖时,倡议把饱受水患的福建省立乡村师范学校从福州洪山桥边迁来,并带头捐资一千银元作为搬迁费用。第二年乡村师范学校就顺利落户了,担任校长的是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的尚干人林葭蕃,学生最多时有四五百人。之后书院陆续数次改名,私立七濑农业中学、林森县立初级中学、尚干中学、祥谦中学等等,却一直不改作为教书育人的文雅场所。
1981年我从师专毕业后分配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落脚这个被称为“故乡”的地方。此时它已再次更名为闽侯县第二中学,校园面积110多亩,建筑面积五万多平方米。刚进校园时,看到宽阔平坦的田径场上,竟孤零零地斜立着一株已枯了大半的龙眼树,这是林祥谦亲手种植的。1988年我调离,在离去很久之后,才知道七年间我所住的宿舍,竟然就是陶南书院和淘江书院曾经的教室。宽阔的白墙、陡峭的台阶、精美的阁楼、俊朗的木构屋以及巨大的天井和典雅的池塘,当时看进眼里都不为意,回想起来却是那般意味深长。很庆幸,近百年后的今天,这一片古建筑群依然矗立原处。经过几次修复,它们成为校史陈列室。书香依旧,文脉未断。
我祖父在镇上的老房子已大部分坍塌。1949年它曾成为大队办公室,大队搬走后,同族的人又搬进住。前几年我重返过,有一瞬闪过要把它们购回的念头,转眼又息下了。我奶奶已逝去53年。当初从这里逃离时她才24岁,如果活着,今年120岁了。
这里的男人如今不知是否还迷恋习武。那天我走访了几处民居,在他们家厅堂、厨房角落发现几个泛着青苔的巨大石墩、石锤、石柱。主人说是祖上练臂力用的,现在无用武之地了,它们只能沦为用作垫水桶或者砌洗衣池。
镇上的江河湖水明显比以前少了,桥却多了,房子更多。1972年横跨淘江的祥谦大桥建成后,进出镇上就不必再靠船了。从桥上一下来,一眼就能看到一座端立在镇口左侧的西洋式双层别墅,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政府专门建起供林祥谦妻子陈桂贞居住的,桥那一头还有一座肃穆的林祥谦陵园。按我奶奶的说法,陈桂贞是她远房表亲,年少时有过交往。1923年2月7日夜,林祥谦被害时,陈桂贞就在现场。当工友把林祥谦残破的尸体偷抬回家时,28岁的陈桂贞用做衣服的针线将其头颅缝合上。她的公公见儿子被害,提着斧头冲出去报仇,也一命归西。同一天被杀的还有林祥谦的弟弟林元成。一家三尸,个子娇小的陈桂贞独自承担起全部。五年后她带着子女和三口棺材走水路回到老家,绝口不提丈夫在汉口发生的一切。没两年女儿又夭折,她跟我奶奶一样,靠给人缝补衣服把儿子养大,助他娶了妻。儿子后来生了四个子女,都在二中读完高中。
所以,《寻找妻子古菜花》中那个倔强的女子奈月,她与这块土地也是一脉相承的。写这篇小说时,也许陈桂贞和我奶奶,都曾在脑中沉浮过。所有写作者似乎都绕不开故乡这个主题,它是根,是土壤,是走向远方的勇气与底气。但因为不在这里生和长,我其实一直怯于触及,几十年来把它写进小说的,也仅有《寻找妻子古菜花》和《龙舟》。以后这里的一切还会再出现在我的笔端吗?不知道,一切都等待机缘。即使再不触及,在心底我都已给它腾出一块地方了。当地的林氏祠堂曾几次打算将我纳入族谱。女人也可以让家族引以为傲,时代真是进步了,但我一丝犹豫都没有就坚拒掉。有些东西一旦外化,反倒会生出几分不自在。我是这里人,流着这里的血,并且同样被这里到处流淌的江水所滋润,这就够了。生命的延续如此妙不可言,无论如何,我们都走不出故乡宽广无边的视线。
(作者:林那北,系福建省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