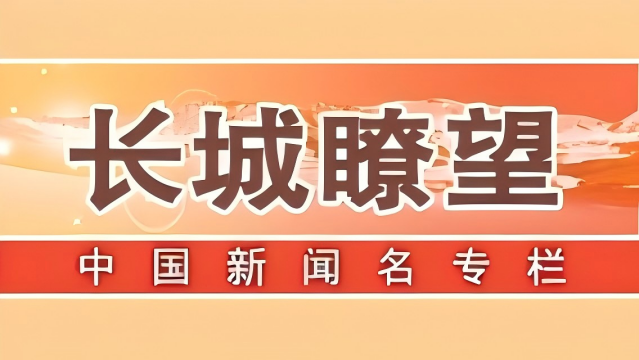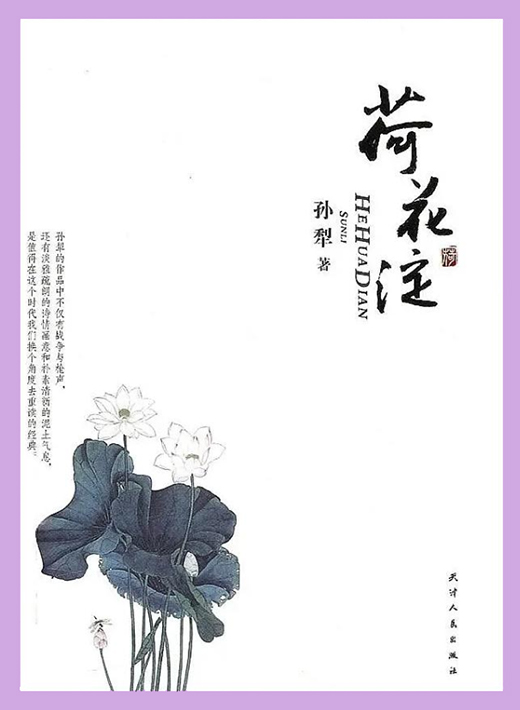
荷花淀
■陈晔
孙犁来安新,绝非偶然。他不是安新人。他的家乡安平离安新和白洋淀很远。是时代,把他推到白洋淀,使他写出了成名作《荷花淀》……
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是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北面是滹沱河,南面是大苇塘。1926年,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从初中起,他就在校刊发表作品。高中毕业,孙犁到了北京,却不适应城市生活,心里有些苦闷,于是离京返回老家。
1936年夏天,孙犁在家百无聊赖。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保定的两位同学给他找了份工作,就在保定安新县。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孙犁离开安平。
他先到了保定与两位同学会合,而后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在同口小学任教。穿长衫、戴礼帽的孙犁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在同口,他教了一年书。村民们都叫他“孙先生”。他没事就去各家串门,聊些家长里短。没架子的“孙先生”让村民顿生好感,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送去给他。过年过节,村民干脆让孩子把他叫到家里吃饭。
课余时光,孙犁喜欢看书,也爱四处走走。若学生家里有船,便会载着他前往荷花淀,一同采荷挖藕。夏日里太阳毒,师生就举一柄大荷叶遮阳。
淀里的芦苇是编苇席的好材料。时常是吃过晚饭,孙犁就来看乡亲们编席。苇席在一双双巧手中上下飞舞,他仔细观察每个细节,在脑海中捕捉相应的词语。
“黑乎乎的,咋不点灯?”
“费油!”
一个嫂子扬了一下手:“那就是灯!”
顺着那双修长的手,孙犁抬起头看,原来是一轮黄澄澄的圆月。他笑了,脑海里定格了一个永久的画面。
这一年在水乡泽国的生活,像画一样刻在孙犁的记忆里。后来许多年里,他不止一次做梦回到白洋淀,想起泛着光的席子,还有女人们编席时翻腾的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孙犁参加了抗日,不久后来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开始提笔写作,走上文艺战士的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们的创作方向悄然转变。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孙犁陷入沉思——该写什么?忽然间,他眼前一亮:是一杆杆挺出水面的荷箭,是高低错落、迎风吐艳的荷花,是如霜似雪的苇花。对,就写荷花淀!他惦念着那里的人们,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们是否已拿起了武器,是否在奋勇抗日。他不断打探着来自白洋淀的消息,终于听说了雁翎队,听说了那里荡气回肠的抗日故事……
他想同口,想“水生”和“水生嫂”。日本鬼子杀进荷花淀,村民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他们拿起枪去和敌人战斗,宽阔的水面,无垠的芦苇,处处是战场!1945年,孙犁写出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一经发表就引起震动,后来还被收入语文课本。很多白洋淀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读到《荷花淀》,都会感叹:“呀,写的是我们安新、我们同口!”
许多年后,当他回到同口故地重游,走在街上时,年纪大一点的人和他的学生还认识他,他们仍旧唤他“孙先生”。他见到了“水生”和“水生嫂”。嫂子们说:“孙先生啊,你的文章写得真不赖。”
少年时我在保定上学,身边不少同学来自白洋淀,她们是“水生”和“水生嫂”的孙辈。周末过后,她们从家里回到学校,带来荷叶包着的鱼虾,还有菱角和莲蓬。她们讲姥姥、奶奶怎么采荷,爷爷、姥爷怎么参加雁翎队打鬼子。她们的肤色带着水乡的润泽,皮肤上似乎蒙着一层水汽,眼睛里漾一种水的光泽,笑时脸上会浮起一层荷花一样的红粉……
这片土地,如今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雄安新区。小说让荷花淀成为艺术标签,荷花淀还在,而且有了时代气韵。
一位在雄安工作的教师朋友告诉我,她给学生上课,常读《荷花淀》:“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