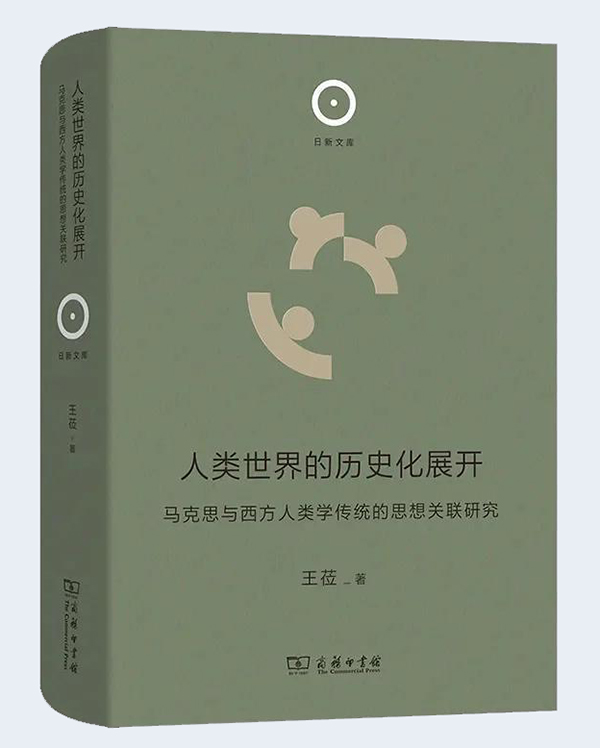
对“作为人类学家的马克思”的探究
■聂锦芳
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在少数的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但实际上,离开西方思想传统和社会发展,不可能客观而到位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起源、演变及其意旨和效应。这样说来,清理和辨析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成为突破既往理念和模式、拓展和深化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内在要求。王莅所著《人类世界的历史化展开——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思想关联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8月出版)体现了这一研究旨趣,并在扎实的文本解读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探究研究马克思与人类学关系何以必要?
西方思想传统本身具有复杂的结构和内涵,过于宏观的把握和大而化之的处理,不利于这一问题的细节甄别和研究的实质性推进,所以选择什么样的视角予以开掘就显得很重要了。王莅正是基于上述思考,选取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关系展开专项探究,借助对马克思具体文本的悉心解读,全面考察了其思想历程中的“人类学因素”,进而阐明人类学视角对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所具有的意义,而这种对二者思想关联的勾勒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人类世界的历史化展开”的生动思想图景。
作者对于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类学传统所具有的思想关联的内在逻辑和依据进行了详实的论证和说明,指出这两种致力于揭示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和科学,在根本上都基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而对人展开认知:共同承认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前提,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实现;二者之间虽然性质不同,但可以完成转化。如果说,发端于古典时代宇宙论的自然主义、脱胎于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分别代表着在过去不同历史阶段人对自身生活世界的秩序思考,那么伴随着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展开,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和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开始重建人的科学,马克思所建构和阐发的“历史科学”即属于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人类学思想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揭示马克思对西方文明现代转型的反思与推进。
马克思思想进程中人类学的“内化”和“融合”
本书最重要的工作是清理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人类学视角是如何“嵌入”“展示”“内化”和“融合”的。自从1972年卡拉德等人编辑、出版“人类学笔记”,并有论者据此提出“作为人类学家的马克思”概念以来,这方面的言说可以说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成果的论证和观点都显得简单、抽象而宏观。本书是我见到的“以文献材料说话”、以思想进程的逻辑展开推演,借此将这一专题清理得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作者的概括准确而精当,论断新颖而独到。
比如,与以往基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分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做法不同,作者借助哲学人类学的视角从人类视域的确立、人类解放的求索和人类历史的展开三个环节勾勒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过程,以此突显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鲜明的实践旨趣。还比如,在现有的马克思研究中,直接基于《资本论》创作背景和理论议题讨论其人类学思想的成果并不多见,因为以现代社会及其经济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与以史前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在直观层面上仿佛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作者通过对《资本论》进行历史化解读,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内涵了历史叙事旨趣,即以经济学逻辑作为人类历史的叙述方法,以共同体诸态描述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以原始积累论打开人类历史的现代入口。
另外,对于马克思晚年摘录的“人类学笔记”,作者既不赞同现今流传的五本笔记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说法,也不认可是一个“理论整体”的判断,而是通过对西方法学传统的考察,认为它们反映出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人类学所聚焦的进化论、古代法和母权论等议题,而这些议题共同解构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的自然法特征,确立了现代人对历史性的信念。据此,一方面马克思进一步确证了不仅现代社会而且人类社会自身都需要通过革命来加以重建,另一方面现实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导致了他晚年思考的多元性和未完成性。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可以在西方思想史及其背后的现实历史演进中加以重新考察,而社会人类学视角便是讨论这一问题的直接起点。综合这些分析和论断不难看出,本书在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类学传统关系的研究上确实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
人类学视角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上述复杂关系的探究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变革及其当代效应具有特别的意义,本书花了近10万字的篇幅对此作了阐释。作者将“作为人类学家的马克思”从一种身份界定上升为一个理论标识,聚焦于人类学视角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互参与、建构,系统说明了西方人类学传统对重新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思想价值。概言之,人类学的问题视角和思想资源不仅为马克思提供了丰富的议题,而且还建构起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人类历史叙事主题上的诸多结论,作者将其概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类学向度”。
具体说来,其一,在人类学视域下,马克思成功地将历史展开的方式从神意安排转向社会生成,将历史叙事的中心从市民社会转向人类社会,将历史创造的基础从古典文明转向史前文化,从而回答了“人类历史”的定向问题。其二,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继承了西方人类学中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并非根本异质的传统观念,通过哲学批判论证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基础,通过历史批判发掘了人类历史产生的自然前提。最后,在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影响下,马克思将世界的时空构序推进到世界历史问题,实现了“世界”与“历史”概念的内在融合,基于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社会普遍深陷经济危机和政治倒退的现实,马克思尝试以史前文化对人类世界秩序进行重塑,以社会进化重新解释人类历史的生成过程,将政治秩序还原为更基础的社会秩序,改写西方文明的“家庭—国家”结构。这样,以“人类历史”“人化自然”和“世界秩序”三者为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获得明确的人类学指向,代表着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相互融合而成的重要理论成就。作者对二者关系细致入微的探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表明,西方思想传统可以为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丰富的问题视角、理论议题和思想资源。
作者在马克思与西方人类学传统关系上能够取得如此扎实的进展和实质性突破不是偶然的。求学期间,他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受过完整、连续、系统的哲学专业训练,少数民族(白族)出身又让他对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保持特殊的兴趣,不仅选修了相关课程,而且长期跟踪这些领域研究的前沿动态,对其历史传统、思想变迁和当代问题有较为深入的把握。2018年作者出版了凝结其多年学习和探究结晶的专著《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受到学界关注。本书则是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成果,两书比较,又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和研究水准的提升。而其中理性的分析方法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显得尤其突出。
经典作品常读常新,卓越的思想家复杂的思想世界更需要基于新的时代境遇和完整而权威的文献不断得以开掘,借助理性的分析方法和严密的逻辑论证阐发出新的气象、形态和意义。本书的探索体现了这一意旨,也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