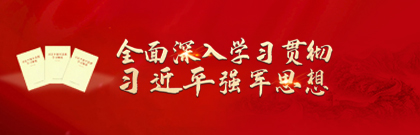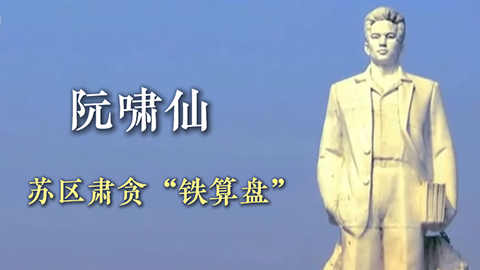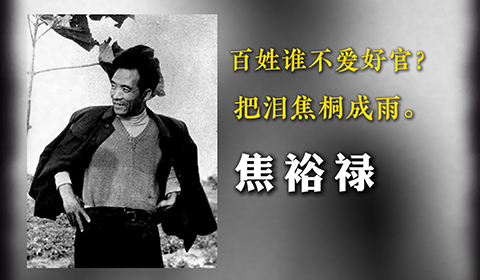欧阳洛,江西永新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担任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书记。1930年3月在武汉被捕,后英勇就义,时年30岁。
一
欧阳洛是江西省永新县中共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和我党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他于1900年11月23日出生于永新县芦溪乡阳家村。父亲是清末秀才。他幼年随父读私塾,后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务农。无论生计如何艰难、农活如何繁重,他始终坚持自学,1922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影响。
当时,一师是南昌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学生运动比较活跃的学校之一。欧阳洛与方志敏、黄道等人发起成立江西“改造社”,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撞击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剖析黑暗的社会现实,宣传改造人生与社会。他们不仅踊跃撰文抨击时政,还积极发动学生参加“南昌文化书社”、“列宁主义研究会”和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影响很大。
欧阳洛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位贫苦的农家子弟、新知识新思潮的追求者成长为具有先进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欧阳洛入党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壮大党的队伍的工作中去。1925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奉命来到吉安第七师范学校任教,利用教学之便,组织和发动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同年8月,欧阳洛回到家乡,针对当时群众文化知识和思想觉悟不高的弱点,在北乡创办农民夜校,在县城创办平民夜校,吸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参加,传播革命思想。在他的引导下,不仅他的大哥欧阳邦、弟弟欧阳济入了党,而且先后发展了王怀、刘真、贺子珍、贺怡等新党员。
1926年7月,永新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新支部成立,欧阳洛任书记。次年4月,永新支部发展为永新县委,欧阳洛又是第一任县委书记。欧阳洛性格刚强,意志坚韧。在他早期革命活动中,遇到过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险阻,但他从不轻言放弃,总是凭借着大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韧力去克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永新县国民党右派勾结土匪武装突袭县城,捣毁革命组织,捕捉共产党人和群众领袖70余人。当时,欧阳洛正在县城福音堂召开党员大会,得到形势突变、事态严重的消息后,立即宣布散会,沉着地组织党员转移。等他安全地送走全部同志时,自己却被敌人包围在福音堂内。欧阳洛躲入教堂的下水道内,一连藏了好几天。敌人十分恼火,明知欧阳洛就躲在教堂内,可就是找不着,他们采取围困的方法,企图将他饿死或逼出来。欧阳洛受尽饥饿之苦,宁可饿死也不出来投降。后来,他从地下水道潜行到河边,在一位铁匠师傅的帮助下才重见天日。一脱离险境,欧阳洛顾不上休息,日夜兼程,花了4天时间赶到吉安,迅速组织了宁冈、莲花、安福3县的农民自卫军,又马不停蹄地打回永新,收复县城。攻陷县城后,欧阳洛终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
1927年8月3日,欧阳洛参加南昌起义后,奉命转移到上海。由于他在江西是名震遐迩的“赤匪”,为了安全,不得不化装昼伏夜行。到九江时,他已是身无分文,只好到处讨饭,历尽艰辛赶往上海。初到上海时,他又人地生疏,找不到党组织,几天没有吃饭,饿晕在黄浦江边,幸好被一名相知的同志偶然发现,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这时,他已骨瘦如柴,不像人样,但他找到江苏省委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立即分配工作。党内同志敬佩地称他为“铁人”。
欧阳洛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的白区地下斗争经验。1927年11月至1929年8月,欧阳洛先后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他针对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党内同志普遍存在胆怯心理和畏难情绪、工人群众斗争情绪不高等特点,一改过去强迫命令和冒险主义等“左”倾做法,主张从密切联系群众和解决群众日常经济困难入手。他带头深入到工人中去,关心工友疾苦,和气对待工人,耐心地讲解革命道理,逐渐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在群众革命情绪提高后,他精心筹划和组织了几次罢工斗争,带领工友打掉国民党反动派操纵的“沪东工人俱乐部”,促进陷入停顿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活跃。
在上海工作期间,欧阳洛与沈凤英相识相恋,后经组织批准,正式结为夫妇。沈凤英又名沈谷南,她是湖南著名烈士沈春农的女儿,当时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做机要联络工作。婚后不久,沈凤英怀孕了。在她最需要丈夫照顾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派擅长于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的欧阳洛前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他嘱咐沈凤英给生下的孩子取名为欧阳申华,随即离开上海奔赴武汉。
二
武汉曾是大革命时期的“赤都”。大革命失败后,这里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刑场。为了坚持武汉白区工作和指导湖北全省的苏维埃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前赴后继、顽强不屈地斗争,数以百计的重要干部遭到敌人残酷杀害。1929年4月,鉴于湖北省委屡遭破坏、武汉白区环境恶劣,中共中央决定暂不恢复省委机关,将省委的职权分别下放给各中心县委或特委,只在武汉设立特别支部。此后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湖北各地党组织实际处于独立工作的状态。
1929年秋,湖北的形势出现转机。这一时期,蒋(介石)冯(玉祥)、蒋桂、蒋唐(生智)军阀混战相继爆发,蒋介石驻鄂部队纷纷调往内战前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相对削弱。与此同时,由于武汉三镇是蒋介石搜刮、输送战备物资的后方基地,战争的巨额费用被转嫁到贫苦工农身上,引起民怨沸腾,三镇工人反抗的怒火在地下运行集聚,酝酿着新的斗争浪潮。
为了抓住有利形势,推动湖北城乡斗争的复兴,中共中央于9月24日决定恢复中共湖北省委,指定7人为省委委员,任命叶守信为书记,何玉琳为组织部长,欧阳洛为宣传部长。当时,省委管辖鄂西、鄂东北、鄂北3个特委和大冶、黄梅、蒲圻、孝感、汉川5个中心县委,以及武汉特区委(由武汉特别支部扩建),全省党员共计9000余名。
1929年9月,叶守信与欧阳洛到达武汉后,立即组建了中共湖北省委,将省委机关设在汉口。由于叶守信、何玉琳经常到外县巡视,省委日常工作和武汉工运工作就落在了欧阳洛肩上。
欧阳洛到汉后,一头扎进工人群众之中。他经过调查,很快了解到:为应付前线战事,国民党武汉当局将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延长至11小时以上,纺织工人的劳动时间更是由每天14个小时增加到了18个小时,一个工人由过去管理一二部机器增加到三四部。随着劳动时间的加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工人工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普遍减少,厂方和资本家经常借故减薪、拖延付薪。同期,武汉物价飞涨,日常生活用品费用成倍增长,糙米价格创纪录地达到18元一担,工人及其家属苦不堪言。欧阳洛向省委提议,从发动工人进行日常经济斗争入手,逐步将经济斗争导入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这一建议得到省委的批准,并付诸实施。
1929年10月1日,武汉福源纱厂工人为反对该厂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无理征收登记费,聚集1000余人,冲进厂董写字间和工整会办公室,迫使厂方答应停收登记费。但是,10月4日发工资时,工人们发现每人仍被扣收了登记费,愤怒的工人、职员及其家属立即组织起来,再次包围厂董写字间,质问此事。厂方勾结军警当局,派来200余名警察进行镇压,叫嚷:“闹事的都是共产党,开枪!”警察当即开枪射击,抓走工人骨干24人。工人抓起铁棍、石头、煤块进行还击。事件发生后,工人宣布罢工,集合200余人包围警察局。国民党武汉当局因战事紧张,唯恐后方生事,暂时采取缓和政策,不仅释放被抓工人和停收登记费,还主动增加工人每天5分钱的工资。
福源纱厂工人从“打”中得来的胜利,对武汉劳工界,特别是纺织行业震动很大。工人们跃跃欲试,希望仿效福源纱厂工人的办法,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他们说:“我们也要打一次!”叶守信与欧阳洛等人商议,决定因势利导,以纱厂工人为中心,组织其他各界工人,将单纯反对登记费的斗争扩展至全面的经济斗争,提出指导工人斗争的5项目标:(1)彻底反对登记费;(2)增加工资;(3)工人出入自由;(4)茶桶由放在职员休息室改放在车间里;(5)茅厕要改良。随着斗争的深入,省委又提出了进行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1)增加工资一角;(2)改变礼拜不放假、不发工资的陋习,礼拜例假照例休息,工资照发;(3)反对屠杀工人,撤出工厂驻军;(4)不准开除工人;(5)反对工整会,工人有权自主组织工会。
武昌是当时纱厂较为集中的地区。欧阳洛冒着被叛徒指认和军警盘查的危险,频繁奔忙于武昌各大纱厂之间,深入到工厂车间,重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工会,与工运骨干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制定行动计划。在他的领导下,武昌第一纱厂工潮后来居上。工人提出“恢复十六年的条件”的口号。“恢复十六年的条件”是指恢复1926年至1927年期间经过劳资谈判工人争取到的基本权利,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工运果实被国民党剥夺殆尽。工整会委员威胁说:“这是共产党的条件,你们提出来要枪毙。”工人们说:“我们不管谁的条件,只知道现在的米比十六年前的贵几倍。”经过斗争,一纱工人取得了停收登记费和年关7天发双薪的胜利。此后,震寰纱厂和汉口泰安纱厂等工人也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欧阳洛在领导工运中的杰出才能和丰富经验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湖北省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一再赞许“春芳同志(欧阳洛化名毛春芳)在职运中有相当的经验”,“毛同志来鄂时,武汉三镇组织正迭遭破坏摧残之后,毛同志乃切实深入群众,艰难困苦,乃是他们的实际领导者。”在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后,欧阳洛提出要突击发展城市党的力量,改变党在农村进攻、在城市退守的格局,促进工人运动与农民斗争、白区地下斗争与苏区武装斗争的平衡发展。具体讲,就是要在武汉各行业工人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同盟罢工,在宜昌、沙市发动码头工人、海员和车夫,在大冶发动矿工,在老河口发动电力工人,在新堤发动扇业工人,在平汉铁路发动机车工人,共同掀起支援土地革命和消灭军阀战争的群众运动高潮。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湖北出现全省性日趋活跃的工潮,其中,仅武汉地区就在此期间连续爆发了铁路工人的索薪和申薪斗争、福新面粉厂的同盟罢工以及石膏、被服、码头、煤业、米业、车夫、水电等行业数十次罢工,打破了武汉自1927年8月2日总同盟罢工失败以来一度沉寂的局面,增强了城市群众的斗争勇气。
到湖北后,欧阳洛还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创造性地开展宣传战线的工作。他根据白区国民党军警特三位一体、严密侦缉的特点,改变过去凭血气之勇、盲目蛮干的做法,要求红色宣传工作者不仅要有不怕牺牲的斗争勇气,还要熟悉工作环境,运用适合地理民情的斗争方式。每次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前,他都要起草和印制宣传品,亲自培训骨干,交待注意事项。活动期间,他要求将宣传人员进行科学分工,望风者要随时注意敌情变化,散发者要用快捷有效的方式迅速发散宣传品,掩护者要在转移时保证公开宣传人员的安全。据不完全统计,欧阳洛领导的宣传部在纪念十月革命节时,散发传单4000多份;在纪念广州暴动的活动中,散发传单40000多份;在反军阀战争宣传周中,印发中共中央宣言10000份、各种标语50000多条。按照欧阳洛的安排,大批党员、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打扮成穿西装的老板、穿工作服的工人、穿制服的警察,将标语、传单送到居民家里、商店门缝里,张贴到阅报栏、省政府门口,甚至塞到站岗的士兵手里,散发到驻军的营房里。这些标语、传单和宣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它们像高亢激越的号角,像闪着寒光的投枪,大大地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斗志,而国民党统治当局却为此惊慌失措,他们哀叹“共产党的宣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三
1929年12月上旬,叶守信奉命撤离武汉,中共湖北省委改称临时省委,由欧阳洛、何玉琳、邓斌3人负责,欧阳洛任书记。这时,中央军委决定加速发动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的士兵暴动,要求湖北省委采取得力措施,配合落实。
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原系西北军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蒋介石为了兼并异己,将五六万人的国民第二军先后缩编为新编第一师、独立第十五旅,引起该部官兵的普遍不满。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在该部建立了党组织,一度发展到70余名党员。1929年夏,党组织发动该部在宜昌起义,后遭失败,郭子明等一批担任军官的中共党员被迫离队,独立第十五旅中的党组织由当时在第五连任排长的程子华负责联系。
1929年秋冬,国民党当局为扑灭鄂东南的革命火焰,决定将独立第十五旅调到大冶、阳新“进剿”红军。程子华得知消息后,即将这一动向通报给在武昌教书的地下党员赵品三。赵品三迅速向湖北省委作了汇报,使省委及时地掌握了程子华这条线索。12月1日,欧阳洛接到中央军委关于组织独立第十五旅兵暴的指示后,立即派赵品三、郭子明赶赴鄂东南,通知正在该地活动的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员李灿、政委何长工,告诉他们独立第十五旅中有党的秘密组织和几十个党员,要求红五纵队立即与独立第十五旅中的程子华取得联系,设法通过士兵暴动的形式,里应外合地瓦解、消灭独立第十五旅。
与此同时,欧阳洛还主持召开省临委会议,作出关于地方党组织配合独立第十五旅发动兵暴的决定,其主要内容包括:(1)阳新除县城外完全是红色区域,大冶也有相当力量,在敌独立第十五旅到达大冶、阳新后应用政治口号与动员广大群众去领导它、影响它;(2)兵暴发动后应马上解决阳新县城和大冶的反动武装,赤化两县全部区域;(3)兵暴成功后,立足大冶、阳新,向通山、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方向游击,创造广泛的游击区域;(4)兵暴起义队伍和当地红军游击队要注意南与彭德怀领导的湘鄂赣边根据地、西与周逸群领导的洪湖根据地、东与蕲(春)黄(梅)广(济)根据地取得战略上的联系。省委将会议决定书面通知中共大冶中心县委,随后又派邓乾元前往指挥。
遵照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红五纵队党委与中共大冶中心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派郭子明到独立第十五旅找程子华接头,里应外合,攻取大冶城。12月14日,红五纵队和红十二军埋伏于大冶城外。深夜,程子华带领两个连宣布起义,将部队拉出大冶县城,而后又与埋伏在城外的红五纵队迎击追赶起义军的敌军,攻入县城,全歼负隅顽抗的残敌。在此之后,驻阳新的独立第十五旅第一营一连和第三营九连士兵,也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成功地进行起义。这些起义部队被编入红五纵队,为创造鄂东南根据地继续战斗。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央军委共同领导组织的大冶士兵起义将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基本瓦解,被党中央誉为“模范式的兵变”。
中共湖北省临委成立后,由于何玉琳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久未回汉,邓斌负责武汉特区委工作无法脱身,省委机关只有欧阳洛一人唱独角戏。国民党特务机关获悉这一情况后,全力缉捕欧阳洛,大批便衣和叛徒出没于通衢小巷、酒楼茶肆、车站旅馆,守候欧阳洛。为了工作,欧阳洛只得不停地变换自己的住所和接头、开会地点,有时一日数迁。即使是在这种极其险恶的情况下,欧阳洛考虑的也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党的工作。他在1929年12月9日凌晨执笔致信中央,信中写道:“此地的工作一天天多,斗争亦是一天天发展,外县的关系亦是一天天密切,自始至终只是我一个人,我一天忙到晚,总是忙不开;此地交通又不便利,过江又不敢坐轮渡,因为环境的关系,早了又不能出动,晚了又不得回来。我在此地行动也有些困难,只是我一个人,弄得认识的人太多,在几个好点的旅馆里天天钻出钻进,这样不但于秘密工作上有妨碍(什么都在我家里,什么都是我一个人),而且在工作上一定会弄出许多不周到、不正确的事情来。这在党的利益上,实在关系很大。如果我一发生问题,没有一个人接替,又要重新来找线索,工作尤其损失。请你们速派人来,拜托拜托!”
根据欧阳洛的意见,1930年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健全湖北党的领导班子,正式恢复湖北省委,由12名委员组织,其中常委4人,欧阳洛任书记兼妇委主任,郭金魁任工委主任,冯任任宣传部长兼农委主任,何玉琳任组织部长。2月18日,中央又决定让欧阳洛以书记身分兼任组织部长,何玉琳调为秘书长。
1930年春,湖北革命根据地面临大发展的良机。这时,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驻扎在湖北及其周围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大部调往内战前线。欧阳洛和湖北省委决定趁此机会,采取跳跃式向外扩张的策略,迅速将过去呈梅花状分布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欧阳洛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做出《军阀战争中湖北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主要任务》的决议,指示:鄂东北的红一军第三十一师向平汉路发展,并与豫东南红三十二师和皖西北的红三十三师取得密切联系,赤化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界地区;在鄂东南开辟根据地的红五军第五纵队,应加速向长江沿岸和粤汉路沿线的鄂城、咸宁、蒲圻等县发展,并与湘鄂赣边的红五军主力取得战略联系,形成彼此呼应的格局;鄂西的红六军应坚定地向长江下游出击,主动与坚持在湘鄂边的贺龙红二军会合,联为一体。这些指示为湖北全省红色区域和红军指明了努力方向,推动了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统一。
在决议中,欧阳洛还就反对军阀战争、武装拥护苏联、组织同盟罢工、发动春荒斗争、扩大红军游击战争、有计划地组织兵变、加强党的建设和青年团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欧阳洛认为,建设一个强大、健全、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党,是实现湖北革命斗争飞跃的关键。因此,在部署全省工作时,他始终强调从斗争中壮大和健全党的组织,提出了改组旧组织、创建新组织、增强无产阶级成分、肃清富农出党、健全各级领导班子、提拔和训练工农干部、反对机会主义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等措施。对于党的白区工作,欧阳洛与冯任吸取过去党的组织屡遭破坏的教训,决定强化秘密工作纪律,规定一般采取单线联系和分散居住、分散活动的方法,不允许互相打听,发生横的联系,尽量避免一人出问题牵动一大片的现象重演。
正当湖北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向前发展、红色区域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的时候,在中央政治局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对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产生了骄傲情绪和冒险思想,决定采取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路线。1930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加紧组织武汉暴动。同时,中央发出第七十一号通告,要求举行筹备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通告称,武汉目前已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焦点和中心,湖北省委要努力在武汉三镇组织政治罢工和政治示威。由于通告提倡通过飞行集会等公开方式宣传组织群众,结果使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暴露,党的组织失去隐蔽,遭到惨重损失。
1930年3月23日下午,欧阳洛在武昌洪山主持召开武昌区委活动分子会议。因会前党内有人叛变,供出开会地点和时间,2时许,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会场,欧阳洛和武昌区委书记邓斌等全部与会人员都被逮捕。抓捕欧阳洛后,国民党当局大喜过望,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将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和武汉三镇各区组织全部抓获。他们想出了一条毒计,将欧阳洛暗中戴上手铐,用衣物盖住,然后强携着在街上行走,后面尾随许多便衣,只要有人与欧阳洛打招呼或接头,便动手抓人。欧阳洛识破了敌人的花招,故意高举双臂,露出手铐。在特务强行按住他的双手后,又在行走时与便衣激烈争辩,以便引起同志们的注意。特务们无计可施,只得将欧阳洛带回监牢。在牢中,国民党军警用尽酷刑,将欧阳洛打得皮开肉绽、昏死多次,也未能撬开他的嘴巴。硬的不行,只好来软的,他们让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位永新同乡前来劝降。“我知道你的来意,你不用枉费口舌。”欧阳洛没等同乡开口,便坚定地对他说,“大丈夫宁死战场,决不投降。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你也要早点醒悟,及早回头!”
对于软硬不吃的欧阳洛,国民党当局绝望了。4月8日,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以“鼓动工潮,散发过激传单”的罪名,在武昌通湘门外公开处决欧阳洛、邓斌、何长清(湖北省总工会工纠部部长)、史汉斌(武汉三镇纺织总工会委员)等4名共产党“要犯”。那天,欧阳洛毫无惧色,走在前面,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打倒国民党!”等口号,邓斌等3人则高唱《国际歌》和之。高亢激越的口号和雄壮低沉的歌声相互应和,引得沿途行人驻足观望。欧阳洛等烈士将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民的事业,在就义前,他们决心用鲜血最后一次激励和鼓舞人民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下去,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一阵排枪响过,4位烈士猝然倒地,汩汩流淌的鲜血染红了通湘门外黄褐色的土地。就义时,欧阳洛年仅30岁。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欧阳洛等革命先烈毕生追求的理想已经成为了今天的现实生活。烈士们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业绩和精神却将被荆楚人民世代传颂,经久弥新;他们的生命将在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延续、伸展。
(周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