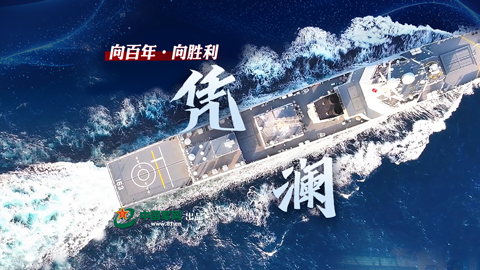七月里的石榴花
■黄世海
初夏时节的崇州氤氲着湿润的雨雾,露萍广场上,张露萍烈士雕像巍然矗立。她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仿佛仍在凝视着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又至石榴花盛开的季节,市民自发聚集在露萍广场,擦拭雕像上的灰尘,献上一束鲜花。而我,作为当年雕像揭幕时的见证者,每每驻足于此,耳畔总会响起那句铿锵有力的川音:“要杀就杀,莫碰我的头发!”
1985年深秋的一天,革命英烈张露萍的家乡崇庆县(今崇州市)罨画池畔,矗立起一座汉白玉雕像。彼时,我在驻地某部任宣传干事。清晨,我攥着刚写好的通讯初稿,火急火燎赶往现场采集细节。当阳光穿透薄雾,为雕像镀上一层金辉时,我分明看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穿越时空,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那段血火交织的历史。
张露萍,原名余硕卿,1921年生于四川崇庆县。“七七事变”爆发后,年仅16岁的张露萍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当年冬天,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的帮助下,张露萍与十余名进步青年秘密离开成都,跋涉千里奔赴延安。
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张露萍勤学苦练,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作为文艺骨干,她常常挥动着双臂,指挥上千人高歌:“河里水,黄又黄,日本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陕北的风沙与抗大的号角,锤炼出张露萍坚定的革命信仰。1938年10月,张露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受党派遣潜入重庆军统局电讯总台,建立地下联络站,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在艰苦环境中,支部发展至7人。
次年春,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面对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等同志始终没有屈服。敌人用尽酷刑,还是一无所获,后将他们7人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7月14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身穿一袭浅咖啡色连衣裙,让难友为她化了最后一次妆,便坦然无畏地走向刑场。在通向刑场的路上,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因身份隐秘,张露萍的英名一度被湮没。1983年,经叶剑英等领导同志证明,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骨迁葬快活岭烈士陵园。如今,张露萍的英雄事迹早已传遍巴山渝水。重庆市歌舞团创作的舞剧《绝对考验》,艺术再现了这位巾帼英烈的革命人生。
七一前夕,我们几位老兵带着软毛刷、抹布和清水,前往露萍广场为雕像除尘。老赵抚着雕像底座感慨:“当年咱们几个一起修改你写的稿子,你总担心我们删减她的英勇事迹!”老李接道:“记得文章刊发后,兄弟部队都来广场开展主题教育。”
我们正谈论着,突然有人凑过来问:“你说,这姑娘是该穿阴丹士林布旗袍,还是该穿灰布军装?”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老者正对着雕像,在画簿上勾勒张露萍烈士的英容。我盯着雕像底座上烈士生平简介里“军统局电讯总台”几个字,一拍大腿说:“你就照着国统区贵妇的样子来,但在什么地方得藏着一颗五角星或一朵石榴花!”
我突然想起张露萍在狱中写的诗《七月里的石榴花》:“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枝头……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我们要去准备着更大的流血,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雨又落了,我轻轻拂去雕像上的水珠。光阴流转,她的笑靥仍如石榴花般炽烈——“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这河流,终将奔向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