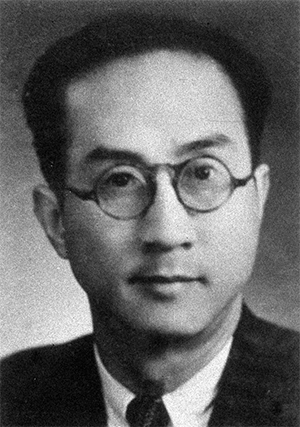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省余江,1895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宽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自幼聪颖好学,智力超人。父亲邹国珍奔忙官场,无暇顾及儿子的学业,母亲为了邹韬奋的前程,从并不宽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为邹韬奋请了一位家庭教师。13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对邹韬奋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我要的是你的学业和前程”,母亲的临终嘱咐时时激励着邹韬奋。他加倍地发奋学习,以此报答九泉之下母亲的养育之恩。
1912年,邹韬奋被父亲送到了工程师的摇篮——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就读。由于从小对文学的酷爱,对新闻记者的执着追求,他不久转入圣约翰大学读文科。当时,经济萧条,物价上涨,父亲失业,家贫如洗,所需费用全靠自己解决。他用自己的勤奋刻苦取得了“优行生”的资格,因而免交学费。他利用课余时间,做家庭教师,向报刊投稿以取得低微的报酬,补贴生活费用。他在毕业时感叹道:“想到平日的苦恼,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筹措学费的艰辛,想到这一天所剩下来的三四百元的债务和身上穿着赊来的西装,眼眶里竟涌上了热泪。”清贫学生时代的经历对邹韬奋以后的一生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20年10月,邹韬奋任《生活》周刊编辑,时年31岁。为了实现早年立下的志愿和理想,他放弃了薪水较高的职业,心甘情愿地把整个身心扑在《生活》周刊的编辑、出版、发行的工作上。他曾这样说过:“《生活》周刊是能使我干得兴奋至致,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从此,邹韬奋走上了新闻出版的道路。
《生活》周刊是邹韬奋主编的刊物中最有影响的一份刊物。开办初期只有两个半工作人员,整期文章都由邹韬奋这个“光杆编辑”包办。他用不同的笔名,撰写各种各样的文章。为写好每一篇文章,他采用“跑街”的方式,把书店当作资料馆,经常光顾,寻找读者需要的信息。一些外文杂志价格昂贵,只得当场阅读,边读边记,整理成文。他身兼多职,既要握笔写作,又要亲自跑印刷厂,看校样,还要答复读者来信。他常常穿梭于工厂、农村、学校,博取丰实的材料,写出了在中国期刊史上首次系统地介绍孙中山坎坷经历及辉煌成就的《听听中山先生的生活》。而以“落霞”为笔名的评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的文章更是广为传诵。
主持正义,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黑暗,这是邹韬奋奉行的办刊宗旨。他以这块小小的阵地替人民说话,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1930年10月间,国民党军阀、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上海为他母亲做寿,花费达10多万元,极尽奢侈。对此,邹韬奋秉笔直书,写了题为《民穷财尽的阔人做寿》一文,以犀利的笔锋斥责了陈调元。第一次从国民政府要员身上开刀,披露透彻,淋漓尽致。很快,不可一世的陈调元成了众矢之的,声名狼藉。1931年8月的一天,邹韬奋拆阅读者来信时,发现了一封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兼大厦大学校长的王伯群利用权势,以数万元聘金纳该校毕业生保志宁为妾的丑闻,并以贪污所得,花50万元巨款在愚园路建私宅藏娇。邹韬奋阅后极为气愤,亲自前往实地探查,并请了一位极有经验的建筑师察看估价,掌握了全部事实,一鼓作气地写出了文章,连同照片一起在《生活》周刊上公开发表,有力地揭露了当权者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多年来,邹韬奋一直希望办一种合乎大众需要的日报,他说:“我生平无任何野心,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但是办好一种周刊是不够的,我们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当他期待多年的《生活日报》出版时,他激动得一夜没睡,“独自拿着微笑,不禁暗中喜出了眼泪”。他一生先后创办了《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7种刊物,出版了几十本著作和译作。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他利用报纸这一新闻媒体发表正确的言论和新闻以唤醒国人,共起救亡御侮。他还公开登报招募股款,支持抗战,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势力作坚决斗争。他因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忌恨,他们对邹韬奋采取软硬兼施,一方面以生命危险威胁他,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利诱他。但邹韬奋早将个人得失与安危置之度外,毅然为抗日救亡,追求真理日夜奔忙。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邹韬奋被选为执委。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无奈之下,邹韬奋登上了意大利邮船“佛尔第”号,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意大利的罗马,法国的马黎,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美国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一段坎坷的经历,历时逾两年。他把在国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汇编成书出版,这就是两部著名的通讯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1935年8月底回国后,邹韬奋更坚定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委。
正当邹韬奋和救国会领导人一起积极推动政府实行抗日救亡国策,为援助绥远抗日而奔走时,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李公朴、章乃器,这就是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同年12月4日,邹韬奋等被押往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来法院对邹韬奋等人提起了公诉,罗织了“十大罪状”,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关注与反响。宋庆龄、何香凝发表声明,许多有名的律师争相表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七君子和他们的律师们跟法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他们大义凛然,理正词严,把审判长们弄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经过法庭上面对面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七君子于次年7月底出狱。
邹韬奋出狱后,立即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主编《全民抗战》,同时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对国民党投降分子作公开、合法的斗争。他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报道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引导大批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
由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以推进大众文化、服务社会为己任,在短短的几年中,发展成遍及全国14个省、拥有56个分支店的全国最大规模的文化阵地。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视他为眼中钉,寻找并捏造了三条“理由”对生活书店加以迫害,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56个分支店中有44个被查封。邹韬奋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化事业的迫害和摧残。抗战期间,他多次去中共中央驻重庆办事处会见周恩来等。皖南事变后,他愤然拟了辞去国民参政员的电文稿。他在电文中这样写道:“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国民参政会号称民意机关,决议等于废纸,念及民主政治前途,不胜痛心,在此种残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无论,韬奋苟犹列身议席,无异自侮”,故决计远离。电文对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残害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严正的抗议。
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将邹韬奋就地惩办的通缉密令。为避免受迫害,邹韬奋历经艰险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同敌人进行的艰苦斗争,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但因重病缠身不能如愿以偿,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秘密回到上海就医。上海党组织对邹韬奋的病情十分关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为他治病。
邹韬奋的病情日趋严重,疼痛难忍,每天靠打止痛针维持。尽管如此,他还是强忍病痛继续在病床上写作,未及完稿的《患难余生记》就是他最后的遗作。重病期间,他仍“心怀祖国,着念同胞”,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仅有一点微薄的能力,提着那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44年7月24日7时20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出版家邹韬奋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说:“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小,20余年追随诸先生,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我死后,恳切要求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的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中共中央对邹韬奋给予了高度评价:“接读韬奋遗嘱,更增加我们的感奋。韬奋先生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副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到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邹韬奋逝世后,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临终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题词。1956年,人民政府决定,在他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上海重庆南路205弄53号建立“韬奋纪念馆”,以志永久的纪念。
(来源:中华英烈网 作者:李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