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故乡的建立和书写
■张生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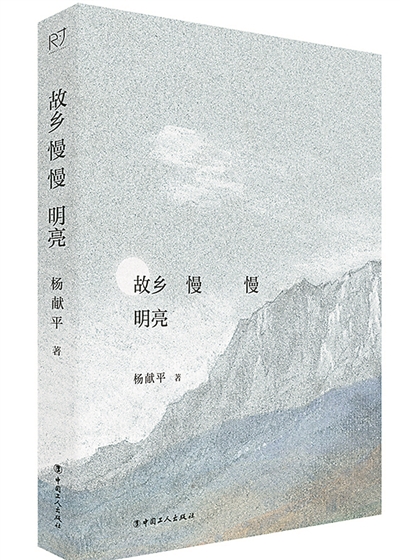
文学地理是作家的第二故乡。这个故乡与一个人出生地的第一故乡不一样,是一个需要重建的故乡。有些作家拼尽一生都无法完成这种重建工作。杨献平是幸运的,他不但完成了重建,还建成了他的从军地“巴丹吉林沙漠”和故乡“南太行”两个文学故乡。
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正是作家杨献平在重建“南太行”文学故乡上的一种尝试。书名中的“故乡”,显然并非杨献平出生成长的那个南太行,而是杨献平建构出来的文学故乡。杨献平说“故乡慢慢明亮”,体现着他在故乡面前的谦卑和在文学写作上的谦逊。
“故乡慢慢明亮”这句话,同时还体现出我作为一个读者同时也是一个写作者,在阅读杨献平作品时的一种心理过程。作为写作者,我在阅读的时候,忍不住会思考一个问题:杨献平是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进入南太行,从而使南太行在他的文学地理中“慢慢明亮”起来的呢?
解读杨献平并不容易。南太行故乡在他的文学地理中“慢慢明亮”,杨献平的文本策略最初在我的心里却并不明朗。
放在卷首的散文是《南太行河山地理》。这篇文章从“千里送京娘”的民间传说开始,引出望君山。作者以望君山为观察点,向后、向西,再把视角集中到山上最高的山峰摩天岭、北武当山,然后抵达作者出生以及长到18岁的村庄。到这为止,一切都还在惯常的写作策略之中。但是再往下看,这线索就如同草蛇灰线,有时候感觉找到了,仔细一看又不是。一方景致牵着,另一方景致又把毛茸茸的卷须伸过来,要把你的视线夺过去。
这种阅读体验,如同往一座大山上去。刚开始,路是明确的,尽管有分岔,但还都比较清晰。然而越往山上走,越发分辨不出前行的路径和方向。消隐这些路径的,是坡上斜逸而出的一树梅花,是路旁堆拥过来的一簇青草,是突然耸立的一座山峰,是炊烟四起的一个村落。渐渐地,抵达这座大山深处时,眼前已不是路,而是山明水秀,是鸟语花香,是随处可见的自然之美。
读到这里,我似乎对杨献平进入南太行的姿态和方式有点明白了。杨献平的写作视角显然不是在空中,如果在空中,他一定对入山的路径看得很清楚,就算偶尔断了,也会根据另一处出现的路,用想象把它们接续起来。这些作品是杨献平踩在泥地上走出来的,是他赤脚行走时的切肤感受,有温度,有疼痛。
在低俯与谦卑的姿态之下,杨献平进入南太行的方式,就是消解宏大的完整时间和空间,而忠实于他的情绪、感觉及个人经验。也就是说,尽管南太行有着漫长的延续不断的历史,有着苍茫浩渺的群峰耸翠,但杨献平只展示他真切感受到的那一块。就如同拿着一把手电筒在黑夜行走,他指向哪里,哪里就明亮起来。杨献平用“故乡慢慢明亮”作为书名,也许是对他写作策略的一种暗示。
对于杨献平来说,细节是摆在他写作中最重要位置上的。这也与杨献平进入南太行的姿态和方式相吻合。他向我们展示的细节是丰富多彩的,既有节令物候,也有人情世故,还有方言土语、历史人文等。
对于细节的描写,一般表述是“精雕细刻”,以此展现细节的质地和光泽。但杨献平对待细节不是这样的,他的方式是“种植”“耕耘”“浇灌”。细节在他的笔下如同种子,他给予它们土壤和阳光,然后看着它们自由生长、抽枝牵蔓。比如,杨献平在写南太行“方言”的时候,他往往会讲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讲一段岁月。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给予这个“方言”土壤和阳光。有了土壤和阳光,这些原本干瘪得像土坷垃一样的方言便吸了水分,返了青,发了芽,摇曳顾盼地长成一棵大树,甚至长成一片森林。
杨献平始终努力做到对细节的极致描摹。本书里有《冷春》《乡村青年朱有成》《最后的矿难》这样的散文,几乎整篇就在说细节。《冷春》讲的是南太行人对于婚姻爱情的态度,《乡村青年朱有成》讲的是南太行人对于一个人事业“有成”还是“无成”的评价,《最后的矿难》讲的是南太行人恒久以来的价值观。细节虽小,但经过作者的苦心经营,显得饱满多汁,给人留下较深印象。
《辞海》中,对“细节”的解释是“琐细的事情”。杨献平笔下南太行人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看来,确实是一些“琐细的事情”。但杨献平并没有轻视这些,他知道这是南太行人“难以描述的命运”“至关重要的事情”“挥之不去的情结”,因此杨献平给予了南太行人足够的尊重。在《最后的矿难》这篇散文中,杨献平写朱福林的母亲有事没事就去朱福林的坟地薅草,然后坐在墓碑旁休息,“风在撕扯着她凌乱的头发,日光落在她额头的皱纹里,好像明亮的蚯蚓,在深深的泥土中不停蜿蜒”。杨献平通篇没有说同情的话,也不附带自己的感情,但在这样的“细节”描写中,能强烈感受到作者蕴含在其中的情感力量。
杨献平这种忠诚而又谦卑的姿态和低俯而又冷静的讲述方式,使得他所建构的“南太行”这个文学地理基础是坚实而厚重的,结构是独特而巧妙的。更重要的是,“南太行”还是生长性的,它在杨献平的笔下生长,也在读者的心中生长。它不但会成为杨献平的“第二故乡”,也会成为我们这些读者的别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