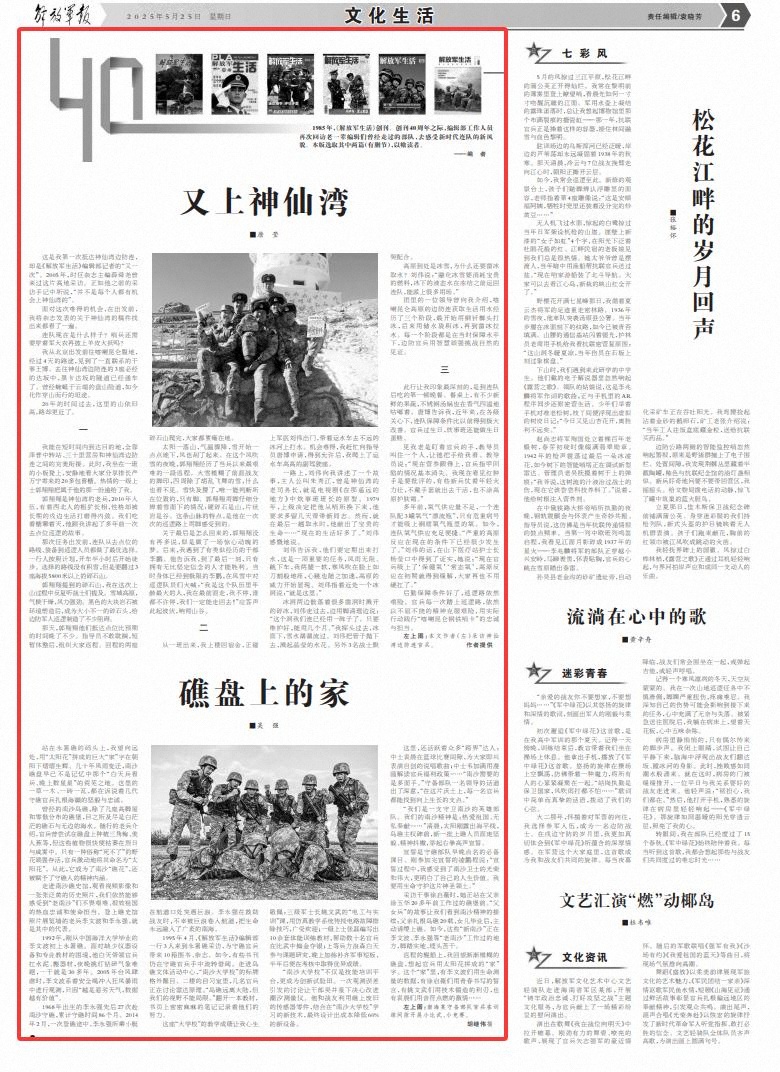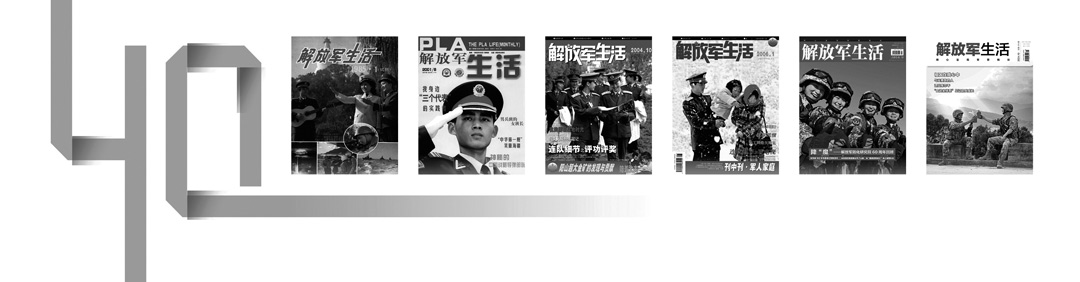
1985年,《解放军生活》创刊。创刊40周年之际,编辑部工作人员再次回访老一辈编辑们曾经走过的部队,去感受新时代连队的新风貌。本版选取其中两篇(有删节),以飨读者。
——编 者
又上神仙湾
■唐 莹
这是我第一次抵达神仙湾边防连,却是《解放军生活》编辑部记者的“又一次”。2005年,时任杂志主编薛舜尧曾来过这片高地采访。正如他之前的采访手记中所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神仙湾的”。
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在出发前,我将杂志发表的关于神仙湾的稿件找出来都看了一遍。
连队现在是什么样子?哨兵还需要穿着军大衣再披上羊皮大袄吗?
我从北京出发前往喀喇昆仑腹地,经过4天的路途,见到了一直联系的干事王博。去往神仙湾边防连的3座必经的达坂中,黑卡达坂的隧道已经通车了。曾经蜿蜒于云端的盘山险道,如今化作穿山而行的坦途。
20年的时间过去,这里的山依旧高,路却更近了。

本文作者(左)采访神仙湾边防连官兵。作者提供
一
我能在短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全靠泽普中转站、三十里营房和神仙湾边防连之间的完美衔接。此时,我坐在一班的小板凳上,安静地看大家分享排长严万宁寄来的20多包喜糖。热情的一级上士郭翔翔把属于他的那一份递给了我。
郭翔翔是神仙湾的老兵,2010年入伍,有着西北人的粗犷长相,性格却被长期的戍边生活打磨得内敛。我们吃着糖聊着天,他跟我讲起了多年前一次去点位巡逻的故事。
那次任务出发前,连队从去点位的路线、装备到巡逻人员都做了最优选择。一行人按照计划,开车半小时后开始徒步。选择的路线没有积雪,但是要翻过3座海拔5800米以上的碎石山。
郭翔翔提到的碎石山,我在这次上山过程中反复听战士们提及。雪域高原,气候干燥,风力强劲。黑色的大块岩石被环境塑造后,成为大小不一的碎石头,给边防军人巡逻制造了不少阻碍。
那天,郭翔翔他们抵达点位比预期的时间晚了不少。指导员不敢耽搁,短暂休整后,组织大家返程。回程的两座碎石山爬完,大家都累瘫在地。
太阳一落山,气温骤降,雪开始一点点地下,风也刮了起来。在这个风吹雪的夜晚,郭翔翔经历了当兵以来最艰难的一段返程。大雪模糊了前面战友的脚印,四周除了胡乱飞舞的雪,什么也看不见。雪快及腰了,唯一能判断所在位置的,只有脚。郭翔翔用脚仔细分辨着雪面下的情况:硬碎石是山,片状岩是谷。这条山脉的特点,是他在一次次的巡逻路上用脚感受到的。
关于最后是怎么回来的,郭翔翔没有再多说,似是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后来,我遇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干部李鹏。他告诉我,到了最后一刻,只有拥有无比坚定信念的人才能胜利。当时身体已经到极限的李鹏,在风雪中对巡逻队员们大喊:“我是这个队伍里年龄最大的人,我在最前面走,我不停,谁都不许停,我们一定能走回去!”应答声此起彼伏,响彻山谷。
二
从一班出来,我上楼回宿舍,正碰上军医刘伟出门,带着运水车去不远的冰河上打水。机会难得,我赶忙向指导员唐博申请,得到允许后,我爬上了运水车高高的副驾驶座。
一路上,刘伟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主人公叫朱秀江,曾是神仙湾的老司务长,就是电视剧《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炊事班班长的原型。1979年,上级决定把他从哨所换下来,他要求多留几天带带新同志。然而,就在最后一趟取水时,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的生活好多了。”刘伟感慨地说。
刘伟告诉我,他们要定期出来打水,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风雨无阻。跳下车,我两腿一软,寒风吹在脸上如刀割般地疼,心跳也随之加速,高原的威力开始显现。刘伟指着近处一个冰洞说:“就是这里。”
冰洞两边散落着很多凿洞时溅开的碎冰,刘伟走过去,边用脚清理边说:“这个洞我们连已经用一阵子了。只要维护好,能用几个月。”我探头过去,冰面下,雪水潺潺流过。刘伟把管子抛下去,溅起晶莹的水花。另外3名战士默契配合。
高原到处是冰雪,为什么还要凿冰取水?刘伟说:“融化冰雪要消耗宝贵的燃料,冰下的液态水在冻结之前运回连队,能派上很多用场。”
团里的一位领导曾向我介绍,喀喇昆仑高原的边防连获取生活用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开始用钢钎榔头打冰,后来用储水袋积冰,再到凿冰拉水。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当时保障水平下,边防官兵用智慧顽强挑战自然的见证。
三
此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连队后吃的第一顿晚餐。餐桌上,有不少新鲜的果蔬,不锈钢汤锅也在香气四溢地咕嘟着。唐博告诉我,近年来,在各级关心下,连队保障条件比以前得到极大改善。官兵过生日,炊事班还能做生日蛋糕。
见我老是盯着官兵的手,教导员叫住一个人,让他把手给我看。教导员说:“现在营养跟得上,官兵指甲凹陷的情况基本消失。我现在看见红肿手是要批评的,有些新兵仗着年轻火力壮,不戴手套就出去干活,也不涂高原护肤霜。”
多年前,氧气供应量不足,一个连队配3罐氧气“漂流瓶”,只有危重病号才能吸上钢质氧气瓶里的氧。如今,连队氧气供应充足便捷。“严重的高原反应在现在的条件下已经很少发生了。”刘伟的话,在山下医疗站护士长杨莹口中得到了证实,她说:“现在官兵吸上了‘保健氧’‘常态氧’,高原反应在初期就得到缓解,大家再也不用硬扛了。”
后勤保障条件好了,巡逻路依然艰险。官兵每一次踏上巡逻路,依然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艰险,用实际行动践行“喀喇昆仑钢铁哨卡”的忠诚与担当。
礁盘上的家
■吴 强
站在永暑礁的码头上,我望向远处,用“太阳花”拼成的巨大“家”字在朝阳下熠熠生辉。几十年风雨变迁,南沙礁盘早已不是记忆中那个“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荒芜之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几代守礁官兵扎根海疆的坚毅与忠诚。

南海某守备部队官兵在训练间隙开展小比武、小竞赛。胡继伟 摄
曾经的南沙岛礁,除了几座高脚屋和零散分布的礁堡,目之所及尽是白茫茫的礁石与无边的海水。随行的老兵介绍,官兵曾尝试在礁盘上种植三角梅、美人蕉等,但这些植物很快便枯萎在烈日与咸雾中。只有一种俗称“死不了”的野花顽强存活,官兵激动地将其命名为“太阳花”。从此,它成为了南沙“礁花”,还被赋予了守礁人的精神内涵。
走进南沙礁史馆,观看视频影像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老南沙”们不畏艰难、报效祖国的热血忠诚和使命担当。登上礁史馆照片展览墙的老兵李文波和李永强,就是其中的代表。
1992年,刚从中国海洋大学毕业的李文波初上永暑礁。面对缺少仪器设备和专业教材的困境,他白天带领官兵扛水泥、搬器材,夜晚挑灯钻研气象难题,一干就是30多年。2005年台风肆虐时,李文波系着安全绳冲入狂风暴雨中进行观测,只因“越是恶劣天气,数据越有价值”。
1968年出生的李永强先后27次赴南沙守礁,累计守礁时间86个月。2014年2月,一次登礁途中,李永强所乘小艇在航道口处突遇巨浪。李永强在救助战友时,不幸被巨浪卷入航道,把生命永远融入了广袤的南海。
1995年4月,《解放军生活》编辑部一行3人来到永暑礁采访,为守礁官兵带来10箱图书、杂志。如今,有些书刊仍在守礁官兵手中流转借阅。走进岛礁文体活动中心,“南沙大学校”的标牌格外醒目。二楼的自习室里,几名官兵正在讨论雷达原理。“岛礁远离大陆,但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翻开一本教材,书页上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着他们的努力。
这座“大学校”的教学成绩让我心生敬佩:三级军士长姚文武的“电工与实训”课,用仿真教学系统传授电路故障排除技巧,广受欢迎;一级上士张磊编写出10余套体能训练教材,帮助数十名官兵在比武中摘金夺银;上等兵方浪森白天参与课题研究,晚上加练补齐军事短板,半年后便在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南沙大学校”不仅是技能培训平台,更成为创新试验田。一次观测误差引发的讨论让干部吴井泉下决心改进潮汐测量仪。他和战友利用礁上废旧的传感器零件,结合在“南沙大学校”学习的新技术,最终设计出成本降低60%的新设备。
这里,还活跃着众多“跨界”达人:中士袁晨在篮球比赛间隙,为大家即兴表演自创的说唱歌曲;中士韦加满用漫画解读官兵福利政策……“南沙需要的是多面手。”守备部队一名领导的话道出了深意,“在这片沃土上,每一名官兵都能找到向上生长的支点。”
“我们是一支守卫南沙的英雄部队。我们的南沙精神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清晨,太阳刚露出海平线,岛礁主权碑前,新一批上礁人员面庞坚毅、精神抖擞,举起右拳高声宣誓。
宣誓是守礁部队早晚点名的必备课目。刚参加完宣誓的凌鹏程说:“宣誓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南沙卫士的光荣和伟大,更明白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要用生命守护这片神圣领土。”
采访干事徐启薇时,她正站在父亲徐玉华20多年前工作过的礁堡前。“父女兵”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南沙精神的接续:父亲扎根岛礁20载,女儿毕业后,主动请缨上礁。如今,这些“新南沙”正在李文波、李永强等“老南沙”工作过的地方,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返程的舰船上,我回望渐渐模糊的礁盘,想起官兵用太阳花拼成的“家”字。这个“家”里,有李文波们用生命测量的数据,有徐启薇们用青春书写的誓言,有姚文武们用技术锻造的利刃,也有袁晨们用音符点燃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