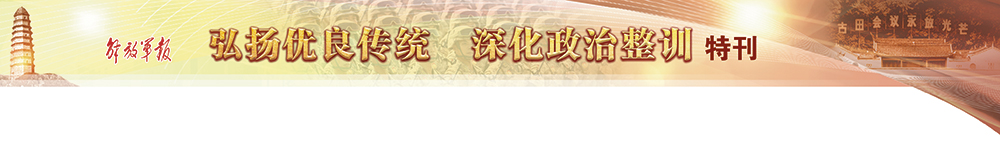
“投身革命即为家”
■剑 钧
那年深秋,我去了赣州梅岭。群山深处,漫山枫叶如血如焰。双脚踩在落叶上,恍若一步踏进1936年的那个冬天。
中央红军长征后,坚守在赣南的红军游击队,由于叛徒出卖而陷入绝境。国民党军大肆搜山“清剿”。一个受伤的身影,隐没在丛莽的石洞里。那凹进去的狭小空间,勉强一人容身,周边敌军的嘈杂声不绝于耳。
“断头今日意如何?”这石破天惊的发问,仿佛还在山谷回荡。洞口垂落的葛藤在风中摇曳,洞旁立有石碑,镌刻“斋坑 陈毅隐蔽处”几个鲜红的大字。
陈毅因腿部负伤,藏身于石壁莽野间,在敌人放火烧山的危难时刻,写下了气吞山河的《梅岭三章》。那是他身处危境中的绝笔,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忠诚熔铸的誓词。纵然身赴“泉台招旧部”,也要“旌旗十万斩阎罗”,读起来是何等悲壮!
人生最大的考验莫过于一死。危急存亡之秋,有人畏死叛逃,有人视死如归,陈毅选择了后者。“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这诗句字字泣血,彰显的是一种大写的忠诚,这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有了这种情怀,南湖红船的点点灯火方能驱走漫漫长夜,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方能聚成燎原之势,延安枣园的油灯方能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此时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留在这里的陈毅却在历经最危难的时日。长征前,为保存中央苏区的“火种”,中央决定部分同志留守苏区。远离红军主力,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谁能挂帅担当这一重任?毛泽东主席提议由陈毅挑起这副担子。那会儿,陈毅因胯骨中弹,久卧病床,行动不便。毛泽东相信他对党的忠诚和坚韧的品格。陈毅留守后,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成功拖住了“围剿”的一部敌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我的目光落在被山火熏黑的岩石上。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陈毅不知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35年春,他带伤率部转战赣南山区,胯骨伤口腐烂了,疼痛难忍。他多次让战士把自己绑在大树上,以便挤出脓血。每回处理完伤口,他会擦去额头的汗珠,继续研究敌情,行军打仗。他深知自己不光是军事首长,更是战士心头的火炬。若连他都显露出动摇,这支队伍何以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中岿然不动呢?
我沿着《梅岭三章》的墨迹回溯,一句“投身革命即为家”,让我从赣南回望到闽西。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内部争论像闽西的雾霭,笼罩着初创的革命事业。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大家所接受和支持。会议选举陈毅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无奈地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同时休养身体。拥有革命远见和责任大义的陈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8月下旬,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发往上海中共中央,后连夜启程,前往上海。
他带回的“九月来信”,如秋日的光澄清了一团迷雾。最动人之处是他在同朱德商量后,亲笔写信恳请毛泽东“出山”:“这次到中央去一趟,我们争论的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检讨。中央已经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的同志也盼望你归队。希望你见信后很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封信的字数不多,却字字恳切,句句真诚。年仅28岁的陈毅,以其艰辛努力,让红四军避免了一场严重危机,推动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从“九月来信”到《梅岭三章》,陈毅用自身行动诠释了他在真理面前,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和以革命大局为重的胸襟。
那天下午,我站在梅岭古道尽头,看远山如浪,暮霭苍茫,唯有漫山枫叶在透进的阳光中熠熠生辉。陈毅曾将“血雨腥风”写进诗句,却坚信“应有涯”。抗战全面爆发后,陈毅担任了新组建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毛泽东电令新四军东进。陈毅面对不同声音,力排众议,率部挺进苏南,创建茅山根据地,打破了“平原不可游击”的论调。后来,他又力主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率先移师苏北,打开了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会师的通道。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至暗时刻,陈毅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新四军在陈毅领导下浴火重生,支撑了华中敌后抗战局面。短短3年间,不足万人的队伍,发展壮大为拥有7个师和1个独立旅、总兵力约9万人的革命武装。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陈毅就犹如梅岭红枫,不惧霜寒,愈冷愈红。历史选择了陈毅,也选择了新四军的未来。
枫叶红得热烈,不是鲜花,胜似鲜花。我想到了《梅岭三章》中“人间遍种自由花”的诗句。从1936年到1949年,仅过去了13年,梅岭红叶就染红了江南大地。1949年春,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到达江苏丹阳,在戴家花园里组织和指挥了上海战役。
也是一个秋天,我去丹阳,在总前委旧址楼前拍了一张照片。我还在纪念馆看到三野陈毅、粟裕等联名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影印件,白纸黑字写明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对此,起初有指战员难以理解:行军借宿百姓家,上门板、捆铺草,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不是历来如此么?可这位即将上任的上海市长回答得斩钉截铁:“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解放大上海的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当市民们打开家门的那一刻,便惊呆了:湿漉漉的马路两侧,睡满了身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这便有了上海人民的口碑:“胜利之师睡马路,自古以来所没有”!
我站在秋意浓浓的梅岭,俯身拾起一片红叶,透过阳光,叶脉如血管般清晰,多么像《梅岭三章》手稿,在战火中熠熠生辉啊。还记得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吗?国民党三路大军进攻新四军。仗打到最紧张时,敌人窜到距我指挥部仅200米处。陈毅一边淡定自若地组织迎击,一边让新婚妻子张茜烧掉所有文件。张茜在烧文件时看到《梅岭三章》,不忍心烧掉,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梅岭三章》手迹。而此战,我军以少胜多,歼灭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1万余人。
临危不乱,坚韧不拔,是陈毅元帅的大将风度;梅岭霜枫,醉染层林,多像陈毅元帅的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