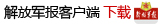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
——《战争论》
一阵带着花腔断音的惊叫从隔壁帐篷传来,把文化干事郄天阙从睡梦中惊醒。他趿拉上拖鞋冲到帐篷外面,高声问道:“怎么了?”
“有……有蜥蜴。”
郄天阙叹了口气,“没事的,蜥蜴不咬人。”
“郄干事你快过来,把它赶走。”这是独唱演员郭炜炜的声音,口气坚决,不容置喙,远不如台上的甜美动人。
郄天阙使劲摇了摇头,像做给谁看一般,然后高喊道:“那我进来了。”
掀开帐篷的帘子,如同掀开新娘的盖头一般,郄天阙总是腼腆地、心怦怦跳地、小心翼翼地,尽管他已经掀了若干次了。
八个女生站在床上,齐刷刷地看着他。四个穿着部队发的体能训练短袖短裤,两个穿着吊带睡裙,一个穿着瑜伽服,一个穿着无肩带裹胸和短裤,左腿和屁股上各一只粉色的小猪佩奇。郄天阙赶紧把头低下去,问:“在哪儿?”
“喏,那里。” 穿着蕾丝边睡裙的曲艺演员吴丽娜竟然用脚尖指着帐篷的一个角落。一只拇指大小的蜥蜴正翘着尾巴用天真无邪的目光看着这几个“尤物”。郄天阙一跺脚,它就翻过低矮的窗口逃出去了。
“好啦,赶走了。”郄天阙低着头,用手撩开帘子的一角,然后鼓起勇气用目光扫过她们,“各位仙女,我多说一句,咱们现在是在战场,大家把衣服穿规整一点,注意影响。”
郄天阙听到有人用胸腔发音,吐出了一声“切”,他瞅了瞅郭炜炜,后者正优雅地翻着白眼,叉开修长的五指做扇风状:“这帐篷里热死了,给我们当馒头蒸呢。”
吴丽娜笑道:“炜炜,你那蒸的是山东大馒头,我们蒸的都是南翔小笼。”话音刚落,姑娘们笑作一团。郄天阙赶紧换了个话题:“大家抓紧午休,下午去六旅砺剑营慰问演出,晚上看他们打弹。”
“真的啊!”“太好啦!”哪怕是这些没正经当过两天兵的文工团演员,对于导弹发射都怀着极大的兴趣。
“快休息吧。”
“郄干事,”吴丽娜叫住他,“芳芳思想有波动,你给她做做思想工作吧!”
一群人又哄笑起来,穿着瑜伽服的程芳芳一边辩解着“哪有”,一边去掐吴丽娜,一群人笑得更大声了。郄天阙也笑了起来,他看了看程芳芳,她正跟吴丽娜打闹着,眼睛却瞟着郄天阙。郄天阙脸一红,撩开帐篷帘子走了。
五月的扎木格沙漠,早晚依旧很凉,睡在帐篷里盖着被子都觉得冷,在外站岗更是要把大衣穿上;而一到了中午就变得很热,毒辣的太阳无遮无拦地晒着,帐篷里的温度少说也有三十六七摄氏度。男兵午休一般都光着膀子,脱得只剩一条裤头,所以她们穿得清凉也并非多大过错。没有给部队找事,没有给首长打小报告,没有相互掐架斗心眼,这帮女演员的表现已经算是出乎意料的好了,文化干事郄天阙安慰自己。
自受领这项任务起,郄天阙就不停地这样安慰自己,他带着这支五男八女的“文艺轻骑队”,从数千公里外的大都市一路辗转,费尽周折总算在前指协调出两间帐篷住了下来。显然,包括郄天阙在内的所有人对这里的条件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女生们带着面包机、瑜伽垫甚至泡脚盆过来,而男生不是没带作战靴就是忘了外腰带,或者干脆把夏季迷彩服带成了冬季迷彩服。纷至沓来的是各种抱怨,比如没有水洗澡,比如旱厕的纱网太透容易走光,比如早餐只有馒头咸菜,比如帐篷太热,比如手机没信号,比如买不到防晒霜和口罩……前指也在抱怨,大家都忙着打仗呢,你们过来添什么乱!哪凉快哪待着去。郄天阙软硬兼施,最后不得不用总部首长的指示来压他们,总算是争取到了为沙漠里的部队巡演的机会。
今天周六,坐在去砺剑营的考斯特上,文化干事郄天阙想,要不是带着这支“天兵天将”,此刻他应当坐在机关大院旁边的“字里行间”就着一杯咖啡看小说,而不是趴在这偏僻、荒凉、不宜生存的沙漠里感受“高技术条件下导弹集群作战的样式”或者探索“现代战争中宣传鼓动和文化保障新模式”。透过后视镜,郄天阙瞟了一眼后面,程芳芳正戴着一个白色的铁三角耳机低着头在背歌谱。她额头光洁,耳垂精巧,鼻梁从双眼之间处延伸,如同沙漠边缘的山脉一般笔直、流畅,未经雕饰;她双眉紧蹙,嘴唇一张一翕,口中默默,神情专注而可爱。在这支各有神通的队伍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腕儿,每个人都在摆谱提要求,唯从她嘴中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没关系”。刚来不久,郄天阙看到一向都是笑容的程芳芳脸上有难过之色,便问她怎么了,吴丽娜替她回答道,“肚子痛”,程芳芳拉了拉吴丽娜的手,又说了一句“没关系”。郄天阙明白过来了,他找到前指负责采购的司务长,请他到镇上买菜的时候顺便带一包红糖回来,然后自己交到她手里。他们的故事便在曲艺演员吴丽娜的口中传了开来……
一个急刹车,考斯特在距离砺剑营尚有三百米的距离停了下来。一名中校带着几名荷枪实弹的战士冲上来,黑着脸让每个人出示证件。演员们面面相觑,郄天阙说:“我们是来演出的,前指没给你们打电话吗?”
“打了。”中校头也没抬,眼睛核对着每一个人和每一张证件,指挥道:“来两个人,把那箱子打开看看。”
“谁敢动!”郭炜炜吼道,“那是演出服装和道具。你们要干什么?不让我们演我们回去不行吗?”
确认车里安全、箱子里没装人后,中校那张黑脸才松弛下来,换了个腔调:“欢迎各位艺术家来我营帮带指导,为官兵送上文化大餐。我是营长曹满江。”
郄天阙的脸还绷着:“曹营长,这就是你们的欢迎之道?”
“我们也是没办法,最近被蓝军搞怕了,都有点风声鹤唳。” 营长赔着笑脸,说,“各位艺术家你们没听说吧,前天中午一个蓝军战士趁着沙暴猫到我们宿营地前沿,在那里潜伏了整整三十二个小时,然后进了炊事班偷了一件迷彩服就跑。”
演员们的脸上稍微好看了一点,吴丽娜问道:“抓到了吗?”
“当然抓到了。”
“人家蓝军干吗偷你们的迷彩服,他没有吗?”
“嘿,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他能偷一件迷彩服,就表示可以窃取你的其他情报;他能进炊事班,就表示可以往水里投毒,在灶台下安炸弹。还好我们发现得早,不然我们营这会儿已经装车带回了。别说打弹,就是想见你们这些艺术家都见不到了。”
演员们终于笑了。吴丽娜问道:“那个兵很厉害呀,你们怎么处理的?”
“这小子,”营长朝沙堆里啐了一口,“逮到后一句话都不说,给他水也不喝,给他吃的也不吃,真把自己当死人了。没一会儿,晕球了。低血糖,赶紧送医院了——不说了,场地都准备好了,那个帐篷里可以换衣服。咱们早点开始,晚上要打弹。”
所谓场地,不过是一个稍微平整的沙堆,战士们围成一圈坐着,队员唱上一支歌跳上一支舞,都让他们眼睛里面闪烁着光芒。他们嗷嗷叫着,把手掌拍得红肿,把装了石子儿的饮料瓶子摇得震天响,程芳芳上场的时候,有个列兵采了一束骆驼草当作鲜花送给她,程芳芳张开双臂想要抱抱他时却被他羞涩地躲开,于是兵们更加兴高采烈地嗷嗷叫着。程芳芳走下沙堆,边唱边朝着圈外走去,十几个战士穿着厚重的防弹背心戴着发烫的凯夫拉头盔站在远处看着,神情肃穆,不为歌声所动。
伴奏过门的时候程芳芳笑着问:“我唱得不好吗?”
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一个列兵说:“我们已经死了。”
演员们都愣住了。营长笑着从圈内跑出来,解释道:“两次遭遇蓝军偷袭,这些人已经被判定阵亡了。”随后踹了那个列兵一脚,训道:“站远点,别丢人了。”程芳芳没有理会营长,拉起那个列兵的手,跟调音的说:“换一首《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战士们齐唱起来:“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那些“阵亡”的士兵也跟着唱了起来。
天色渐渐黯淡下来,一声凌厉而短促的哨响,营地里瞬间安静下来。营长神情严肃地宣布前指发布的气象警报,十五分钟后,此区域将有大风和沙暴,瞬时风力达十级,所有人马上乘车转移到三号阵地。
“呼啦”一下,战士们全都散去,留下还没缓过神来的演员们。各式车辆迅速点火,发动机轰鸣,柴油味道弥漫在营地周围,数十秒后,扛着背囊穿戴整齐的士兵们开始登车,营长冲着“轻骑队”吼了一句:“还等啥?等着被沙埋吗?”
演员们这才狼奔豕突,匆匆忙忙抱起演出服装、道具和音响钻上了车。郄天阙指挥司机道:“跟着部队走吧。”
“郭炜炜呢?”一个声音响起。郄天阙心里一紧,果然少个人,已经跑出一公里的考斯特停了下来。
“完了,她刚刚在帐篷里换装,没听到外面的动静。”
“掉头!”郄天阙指挥道。
后面的猛士车跟了上来,砺剑营二连长胡凭栏伸出头来,问咋回事。
“落了个人。”
“操!”胡凭栏吼道,“你们朝前走,我去找。”
郄天阙想拉住他,猛士车已经往回驶去。顺着猛士车的方向,郄天阙看见远处的天地之间,一股巨大的土黄色的波浪,像壶口瀑布一般向这边卷来,顷刻间,郄天阙的心里被无穷无尽的懊悔填充了。
“胡凭栏!”车没停稳曹满江就跳了下来,扯开嗓子吼道。
沙暴过后的场景原来和洪水过后的场景如此相似。营地一片狼藉,帐篷没有一顶是立着的,干粮和蔬菜散落在目光所及的任何角落。
“二连长!”曹满江又吼了一句。
“郭炜炜!”郄天阙跟着喊了一句,曹满江回头瞅了郄天阙一眼,眼神里恐怕蕴藏着一枚洲际导弹的当量。
嘤嘤的哭泣声从一个倒塌的帐篷里传来,曹满江带着人冲了上去钻进帐篷的帘子,找到了喘着粗气的胡凭栏,此刻一根帐篷的顶梁正压在他的小腿上,他的身下,是惊魂未定的郭炜炜。见到曹满江,郭炜炜哭得更大声了,曹满江不耐烦地招呼两个兵挪开那根顶梁,架走瘫软的郭炜炜,随后冲胡凭栏问道:“能不能动?”
胡凭栏依旧喘着粗气,抱歉地摇了摇头。
“操!”曹满江骂了一句,吼道,“卫生员。”卫生员跑过来,摸摸二连长的腿骨,胡凭栏嗞嗞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卫生员摇摇头说:“怕是骨折了。”郭炜炜趴在程芳芳身上大哭起来。
曹满江把帽子狠狠地砸在地上,拼命地挠着头:“马上就要打弹了!”
“营长。”郄天阙拍拍营长的肩膀,却被营长的手肘推了一个踉跄。
“营长,我很抱歉因为我们的人导致你们减员。”郄天阙把火压在心底,“当务之急是把胡连长送医院,另外,我申请替补胡连长参加发射。”
“你?”营长从鼻孔里使劲地哼出一声,说道,“秀才,你以为是在办公室架着投影仪推材料呢?你知道导弹车有几个轱辘吗?你知道——”
郄天阙打断他:“我之前在长缨旅发射营待了三年,两年排长一年连长,跟咱们一个型号。”
曹满江这才开始从上到下打量着他。
“一号手,接通电源,电源灯亮……”郄天阙用了五分钟,把连指挥员的操作规程清晰完整地背完,这会儿曹满江的脸已经拨云见日了。
“我工程大学毕业的,大学就是学的这个型号,后面才转岗搞政工。”
“那真是可惜了!”曹满江笑道,“完成任务请你吃手抓羊肉。”
三十公里外的准葛力克小镇卫生院里,下士林冲冠正闹着出院,一个中尉被担架抬了进来。
“哟,这不是昨天偷袭我们的蓝军嘛!” 胡凭栏疼得龇牙咧嘴,看到林冲冠却笑了。
“领导,你这是咋回事啊?不会被我们弟兄打折了腿吧?”
“就你们那点偷鸡摸狗的小把戏,能伤到我胡连长?”
林冲冠笑了:“那你这是咋回事?”
“唉,跟一个文工团的女演员钻帐篷,动作太大被顶梁砸到了。”旁边的护士,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说,你这么着急出院干吗?陪陪本连长呗?”
“不好意思,我还得出去继续虐你们。”
“来不及啦!”胡凭栏看看表,“马上就要打弹了。”
说话间,六条笔直的弹道相继从镇卫生院一楼破旧的木质窗台下爬了上来,缓缓升起,像一根根银线在深蓝的天幕上穿过,中尉胡凭栏的双眼放着光芒,下士林冲冠的双眼放着光芒,两个回族的女护士那黑葡萄一般的眼睛里也放着光芒。
(《 沙场》节选)
《解放军文艺》·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