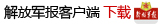不经风浪,何以言勇?
支队很年轻,才17岁,没有传统又最有传统。支队首舰集中了从海军部队抽调的精英,各部队的好传统也在这里融合。吕东方政委当时参与了首舰舰员的选拔工作。他说:“组建首舰其实是为一个新支队储备干部,首舰副舰长一下就配了6名。舰班子成员是百里挑一,一般舰员也是优中选优,78名军校应届毕业生,非党员不要,非优秀学员不要,非兼职学员队干部不要。259名首舰舰员后来被称为‘种子舰员’。”如今支队的舰长、政委,大多是“种子舰员”。
与“种子舰员”对应的是“首舰精神”。
首舰第一次党委会是在舟山至上海的“南湖”号客轮2A207舱室召开的。因部队成立大会一结束就要赶班轮,到上海后,舰员就要分赴大连和武汉学习外语。党委的第一个工作目标,就是带领全体舰员闯过外语关,为赴国外培训打好基础。
这个目标实现了。外聘的外语教授评价说:“你们用一年时间达到了通常需要三年才能达到的水平。”原因何在?狭路相逢,时不待我。时任副舰长的许海华说:“大家不是为文凭、为考级、为留学而学,而是为战斗而学。学不好,就有负军人使命,就会被淘汰。”
一天,首批舰员请外国教员吃饭,请求他多教些内容。吃完了,人家却说:“不要有钱了就行,要强大,拳头还得硬。”话虽难听,却是至理。为了“拳头”能硬起来,吃点苦算什么?受点气又算什么?
首舰副政委傅耀泉回忆:“在外国的海军军校,每天安排8节课,没有什么理解消化的时间,培训所用教材和学员的课堂笔记本,下课时还必须统一收回送保密室。这些情况,反而促进我们学习,各专业人员回到寝室,一起回忆上课内容,共同研究疑难问题,靠记忆‘复原’课堂笔记,每天讨论到深夜……”
1999年5月9日,在中国宁波老火车站,第二批赴国外培训的官兵将在这里坐车到北京转机,东海舰队一位副司令员前来送行,他沉重地说:“你们去该怎么学,我不多说,但我要求你们永远记住昨天发生的事。昨天,美国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他加重语气强调:“要记住,这是中国军队的耻辱!”
“知耻而后勇”,勇者不计私仇,不忘国耻。这支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官兵不忘那一组组屈辱的数字:1860年,英法联军2.5万人,竟长驱直入北京……1900年,不足2万人的八国联军陷落北京,清廷赔偿白银4.5亿两……旧耻不应忘却,新辱更要牢记。要雪耻,就得拼命学。
7个月后,这位副司令员再次来到国外,他是以首舰验收委员会成员和接舰归国航渡总指挥的双重身份来的。该接首舰回国了。有人提出为安全考量,最好租驳船把新舰运回来。“绝对不可以!”总指挥激动地说:“要驳运,我丢不起这个人,除非不让我当这个航渡总指挥。”
自己开回去?没有勇于担当的魄力想都别想。12500海里的航程,要途经大西洋、印度洋,穿越12个海区,10个时区、10个著名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将是我海军首次在北纬60度以北海区航行,首次穿越零度子午线并穿越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红海,首次停靠欧洲、非洲国家港口进行补给,还将首次在离祖国6000海里外与补给舰会合。这么多首次,谁能说得清这中间有多少波谲云诡?
这注定是一次险恶的航程。一出某国领海,一些国家的战机就像苍蝇一样盯上来了,飞得那个低,可以清楚地看到飞行员的脸。波罗的海的狂风巨浪已把他们颠得七荤八素了,而大西洋上的比斯开湾更是用11级大风来迎接他们。8米以上的巨浪,超过18米的长涌,军舰左右颠、前后簸,舱内非固定物品被毫无规律地抛起来,又摔下去。关键时刻,总指挥果断决定沿海岸线航行。有人提出改变航线必须请示批准,总指挥回答:“在危机时刻,指挥员应临机决断!”次日,他们停靠法国布勒斯特港后得知,共有11艘万吨轮在比斯开湾的此次大风浪中沉没。
地中海、红海,再到亚丁湾,首舰终于与国内派来的南运953号补给舰会合了,可高兴劲没过,在进行纵向补给时,油管突然脱落,掉下去缠住了右螺旋桨。军舰废了一条“腿”,还能走吗?必须派人潜水下去,割掉油管!所谓“近处怕鬼,远处怕水”,当时我军对亚丁湾还一片茫然,只知此处水深6000米,水温11摄氏度,海盗横行,时有鲨鱼出没。这样的情况,潜水风险显而易见。机电部门的官兵好多是潜水员,无一人后退,都抢着要下去,总指挥与他们逐个交谈,最后选中了海军工程大学来的学员董新华。董新华不负众望,在水下作业90分钟,排除了险情。
42天风雨兼程。2000年2月14日,首舰停靠在舟山某军港码头。除了安全归建外,还有两大收获:第一,把随舰的外文资料翻译出来了;第二,把部署表完善了。部署表是啥?可以简单理解为电脑的操作系统,包括编制表和运转统筹图。这是引进舰中的一个插曲。照理说,买了军舰同时也就买了部署表,而外方却要另外加钱。国家辛苦挣来的外汇岂能随便花?首舰舰员就自己动手,在不断操演、改进中探索出了几十种部署。
现在,首舰接回来了,部署表也搞出来了,该庆祝一下了,该给家人和朋友报到了。那时舰员没有手机,岸上有一排电话亭,大家争先恐后直奔而去。
有人在电话中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这些名字乍一听有点怪,如:一个男孩叫“彼得”,不是崇洋,也无关耶稣,只因他出生时父亲在圣彼得堡的课堂上;一对双胞胎一个叫“远”,一个叫“航”,因为他俩出生在父亲驾舰归国的日子里。曾亮是唯一在学习外语中收获了爱情的舰员。外语教授是从辽师大聘来的,一次与辽师大外语系学生联欢时,他与女生张威碰出了火花。此刻,两人在电话中谈笑风生。突然,他听到了哭声。那是一个约好一起来给未婚妻打电话的战友。咋啦?“我本想给她一个惊喜,可她却成了别人的新娘。”他在抽泣,战友张松华则是放声大哭,他在国外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在电话中告诉他,父亲临终时还喊着他的名字;大哭的还有与张松华同一个车皮到部队又同年考上军校的郭勇,他父亲也去世了。
引进4艘舰的归国航程,许海华都参加了,头三艘当副舰长,第四艘当舰长。他的孩子出生在他第一次赴国外学习期间,而第4次赴国外前夕,孩子在杭州的医院做手术,他是在医院与妻儿道别的。说起对不起孩子的事,自信开朗的他眼圈红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军人哪个不欠家人的账?”
这一个个故事,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首舰精神”。而精神,包括勇气,是在大风大浪中磨练出来的,光靠教育是教育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