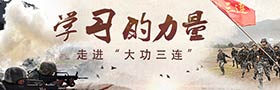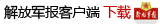内容提要:
特朗普政权将如何改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成为检验美国大战略的试金石。从“特朗普现象”来看,美国孤立主义倾向表明美国对霸权思维方式的变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收缩”;从“特朗普冲击”来看,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思维范式、战略优先度的考量以及秩序塑造方式等,都有新认识和新变化。这些客观上决定了特朗普政权将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予以转变与重塑。总体上看,特朗普政权的亚太战略的调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亚太治理方式、方法的变革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美国霸权逻辑和战略理念转变或转向的问题。
特朗普政权如何定位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如何改变美国的亚太政策的方向、如何塑造亚太秩序问题,事实上已成为影响乃至解决亚太地区诸多问题方程式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变数。在奥巴马政权的“政治遗产”中,“重返亚太”政策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最具有“奥巴马特色”的战略。特朗普政权对这一政策的态度,不但涉及再平衡战略的命运,也涉及他对“亚太”的战略定位,更涉及对美国霸权的思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亚太治理方式的再调整。因而,特朗普不论是维持、调整,还是放弃、重构当前的亚太战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亚太治理方式、方法的变革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美国霸权逻辑”和战略理念转变或转向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东亚日益崛起、美国相对衰落,以及国际权力转移大势所趋的情势下,美国的亚太政策及战略已成为检验美国霸权维持战略的试金石、透视美国总体战略调适的风向标。
1、“特朗普现象”:美国孤立主义的回归与再生
2016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之初,就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担忧”。特朗普竞选的成功,更使这种担忧持续“发酵”。
(一)三种层次的“特朗普现象”
“特朗普现象”原本是对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在共和党候选人中异军突起现象的一种表述,以此说明美国社会、政党政策以及意识形态变化所表现出的“另类”性、异质性的特征。然而,特朗普的竞选成功却使这种“另类”性、异质性意识迅速成为世人眼中的某种“普遍性”。这种意识的转变也使“特朗普现象”从一开始针对共和党、特朗普本人,扩展为针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再认识,从而使这种现象“升华”为另一种“特朗普现象”。非但如此,在英国脱欧、美国内向化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已成为2016年的另一个“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现象”已经不只停留于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生态中,它本身又成为人们重新思考美国与世界、世界与美国关系形态的一种方式。“特朗普现象”与“黑天鹅事件”的深度重合,使得人们对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和美国战略的转变充满了些许未知和忧虑。
三种“特朗普现象”或者说“特朗普现象”的三个维度,折射出美国大选以及美国政权交替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程度各异的影响。但不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说,特朗普所主张的“美国第一”本身就是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最明显的标识。早在特朗普被提名为共和党竞选人之初,一些国家就意识到“特朗普要使美国重返孤立主义”。不过,这种担忧只局限于对特朗普本人以及共和党的特朗普支持层。此后,随着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人们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担忧也逐渐加重,但总体上都认为特朗普本人的特性以及其政策的特质不会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尽管有所担忧但都有“隔岸观火”式的超然处之的“自信”。这时间,对特朗普本人及其政策的批评、批判,事实上旨在于警示美国民众不要选择秉持孤立主义的特朗普。大多数人都认为,“不选择特朗普、不选择孤立主义”应是这个“世界霸主”美国和有着“天然使命感”的美国民众,以及基于所谓“上帝选民”治下的“山巅之国”政治合法性“计算”而得出的“必然结果”。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特朗普自身的政策特性,即便有一定的支持基础,但并不能改变什么。孤立主义有它存在的土壤,但更多地反映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层面,不可能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指导理念。由此反向推理美国的孤立主义路线“不切实际”,这也就决定了特朗普不可能成功。这种思维,事实上成为预测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的一种“定式”。不但外国评论者这样认识,美国的一些政策人士也这样认识。在美国55家权威媒体中,只有两家看好特朗普。而在有些国家的预测中,绝大多数都认为希拉里“大胜”特朗普“绝不是一星半点”。由此可见,“特朗普现象”打破并超越了人们所谓的“常识”,是名副其实的“黑天鹅事件”。
(二)三种所谓的政治“常识”
特朗普竞选的成功,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以上所说的这个“常识”。这至少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或层面来看:
第一,关于特朗普的“常识”。从特朗普个人经历、特性、竞选政策主张看,他本身介于“常识”与“非常识”之间。“常识”之处在于成功的商人参与美国“金钱政治”之中并依靠其资本、资金的支持、依靠其商业成功的“示范效应”、依赖其在大众媒体的传播中累积“人气”而获得成功,这在美国政治、总统竞选中属于“常识”。缺少这些,没有哪一个竞选人会成功。但问题在于,特朗普张扬个性以及类似“特朗普大学”那种商业机会主义的方式,在战后竞选人中绝对属于“异类”。而且,特朗普没有政治生涯的经历、缺乏所谓“政治世家”式的背景,他凭借“没有其他任何竞选人比得上的‘政治不正确’尺度”和“彻底改写共和党的定义”的唐吉坷德式的竞选策略成功登顶,这绝对是“非常识”的。不过,反而观之,既然美国的体制允许这样的人物成为候选人,共和党的政纲允许这样的代表诞生、美国社会变革呼唤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这也就决定了特朗普本人既不是绝对地被排除于所谓的政治“常识”之外,又非完全地置于这种政治“常识”之中。
第二,关于“特朗普现象”的“常识”。这一所谓的“现象”,从最初开始就是从特朗普本人个性的视角而非其政策主张的视角来定义的。在精英的视野中,“特朗普现象”这个概念背后隐含有这样“常识”性的“共识”: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国第一”式的孤立主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却很实用;但是,特朗普却未必这样,他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绝对不会成为美国总统。时至今日重新思考这一概念才发现,从一开始人们就戴着“有色眼镜”走进了一个误区。人们简单地认为:孤立主义行不通、特朗普个性决定他的竞选不会成功 最后两者相加的结果是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孤立主义也绝不可能。直至特朗普当选,人们还在纠结于特朗普的个性、成功的“不可思议”问题上,并没有对“特朗普现象”重新思考。如果回顾美国总统大选,1993年克林顿打着“国内优先”的旗帜,高喊着“笨蛋!是经济。”的口号进入白宫,这种政策主张恰恰与今天的特朗普“美国第一”、“让美国变得更强大”异曲同工。从这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用希拉里丈夫的策略击败了希拉里。2004年总统选举小布什则以“道德牌”战胜了克里的“经济牌”,仍是超出许多人的想象。2008年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帜,喊着“撤军”、“结束反恐战”、“让美国(军)人回家”的口号战胜麦凯恩,仍压倒了对“有色人种总统”可能存在的“政治正确性”的质疑。那么,为何唯独特朗普被置于“现象”位置,且在竞选成功后仍被揪着不放呢。可以说,这本身就是“非常识”。归根结底,这是许多人用所谓的“非常识”性“常识”来看特朗普本身政策的合理性的“常识”,并夸大了特朗普本人个性的“非常识”而造成的必然结果。
第三,关于美国政治及其对外政策的“常识”。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一书是美国政治的经典之作,是塑造美国精神、确立美国独立立国之根本的奠基之作。《常识》一书的精髓就在于为独立革命时期美国确立了“美国道路”。此后,美国建国之初的孤立主义政策、二战前的“中立主义”政策、二战中及其后的结盟政策、二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等,都相继成为一个又一个美国的“常识”。2016年,当特朗普打出“美国第一”标识后,对美国孤立主义回潮的担忧悄然增长。此后,在特朗普强调“若当选总统,我的外交政策将大大不同于二战后的共和党传统”、“等我上台后这一切就会改变”、“我们与对手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将美国列在第一位,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将成为我们的信条”、“应用‘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之后,人们才发现令人“担忧”的不只是美国回归孤立主义,他要变革的是美国二战后的体制安排、挑战的是共和党的传统,矛头指向的是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似已根深蒂固的“常识”。
从《常识》来看今天的所谓“常识”就会发现,对特朗普的众多非议反映出人们对美国的“矛盾心态”。一些人虽然对特朗普的政策心存担忧,但又乐观地认为他的竞选政策与施政政策会有所区别,美国政治体制会限制或规范“总统特朗普”的行为;一些国家对美国重返孤立主义心存芥蒂,但同样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持警惕;一些盟友担心特朗普会改变对盟国的政策,但同样不希望美国过多干预盟国事务;西方一些国家对特朗普要改变战后安排持有戒心,但同样不希望美国像战后初期那样行事。因此,对特朗普的批评和批判实质上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上:一个是如何看待美国的霸权,另一个是如何评价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道路”。众多的美国盟友之所以对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反应敏感,就在于他们不希望美国“超级霸权”,但却寄希望美国继续“领导世界”,认为维持战后的国际机制安排(包括联盟政策)才是“美国道路”的最基本的常识,而特朗普可能会改变这一道路。从这样的视角看,大多数的特朗普批评者,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们更将维持战后体制的“惯性”、习惯或遵从“美国的世界领导”当作了一个“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