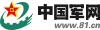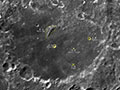齐: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草原歌曲影响越来越大,认可度越来越高,可以说是风靡大江南北。您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
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认真探讨。就我本人来看,这可能与草原歌曲自身的一些特点有关。草原歌曲的一个特点是它的通俗性,歌词通晓明白、生活色彩深厚,旋律也自然流畅,与呼吸起伏的韵律、人体脉搏的韵律、飞马奔驰的节奏是高度契合的,唱起来上口,听起来也很舒服。许多草原歌曲都是广场舞的伴奏曲,原因恐怕也在这里。再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抒情性强,草原歌曲叙事的少、写景的少、抒情的多,即使是叙事写景也只是个由头和载体,主要还是为了抒情,所以它能够更好地引起大家的共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地域性。草原的特点是天高地广、幅员辽阔,所以它孕育出来的歌曲的意向也是很开阔的,它抒发的不是小桥流水的感情,不是江南民歌那样精巧、细腻的感情,而是千里放歌、万马奔腾的感情,它也许不够精致、不够细腻、不够温婉,可能也不够优雅,但是它更开阔、更博大,它表达的是一种“草原情”。
齐:您的分析很有道理!通俗性、抒情性、地域性应该不是内蒙民歌专属的特点,而是各地民歌的共同特点,但草原这种特定的地域,给草原歌曲的抒情性赋予了不同的质地,与“天大地大”相适应,它宣泄的情也是一种“大感情”。许多优秀的草原歌曲都有一种非常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比如《牧歌》,将高远的蓝天大地收在眼底、握在手中;比如《蓝色的蒙古高原》,把广阔的高原作为具体场景的参照系;再比如《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将山河大地、父母亲情,自然景观、人文情怀作了一体化的处理;在这方面,韩红的《莫尼山》应该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听她用蒙语演唱这首歌,虽然听不懂歌词,却可以更专注地领略它的意境,更能感受到它感情上的旷达豪放丰沛——真是格局非凡、气魄宏大,了不起!
龙:“草原歌曲热”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了,的确应该有人从歌曲以外、音乐以外,进行专门的研究。
齐:此外,忧伤也是草原歌曲感情内涵的一个重要元素。西藏、新疆也是盛产草原歌曲的地区,但相对来说,西藏的草原歌曲比较清新明朗,新疆哈萨克牧人的草原歌曲更多的则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欢快,而内蒙古的草原歌曲,即使表达的是一种硬朗的情调,也会有一种淡淡的伤感渗透在里面。比如腾格尔的《蒙古人》《天堂》,唱的是赞歌,听起来却像挽歌,经济在发展但草原却在萎缩,有灵魂的歌者对此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哈扎布过去经常唱的几首歌《小黄马》等,则是忧伤的“咏叹调”。您唱的《陪你一起看草原》,旋律中也弥漫着一种似有若无的感伤情调。
龙:是的,比起农民市民来,草原上的人们是直接面对自然、触摸自然的,天地那么大,人那么小,在这种环境下艰难成长的草原人,既是豪放的,也是忧伤的。孤寂、艰难的生活,表现在音乐上,可能就是忧伤的长调。
齐:但现在草原歌曲的受众恐怕倒是“城里人”更多一些(没有统计数据支持,只是一种直感)。城里人面对的生存困境(至少是困惑),更需要既豪放又忧伤的草原歌曲去舒缓和慰藉,现代化、城市化的困境使许多人产生了精神上回归的倾向,向草原回归,向前现代回归。就人类整体而言,茫茫大草原上的生存轨迹是他们一段重要的历史。一定意义上说,草原是人类的母体,游牧生活是人类早期的生活方式,但游牧生活是艰难的,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下顿,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游牧民族终于被超越,定居下来了,成了农耕民族,人们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生活,然后进一步发展,部分村落成了集镇、成了城市,农民变成了市民。但人们渐渐发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高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眼花瞭乱、无所适从,人们不知道何时会被迅速发展的时代列车甩掉,不知道他们明天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表达这种生活方式困境和生存压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倾听草原歌曲,在想像中回到草原,让大草原的清风、阳光、花花草草爱抚自己。
龙:您的解读很浪漫也很感人。按照您的说法,草原歌曲还有医治缓解“城市病”“现代病”的作用。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作为一个歌者,我也不敢将歌曲的作用说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