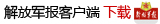自古以来,一支军队的变革往往影响一个国家的兴亡、一个民族的盛衰。
公元前307年的赵国,年轻的国君赵雍带领他的一干大臣接连在边境巡视。回到国都,一个消息爆出,国君带头穿上胡人的衣服,而且要在军中推广。这在中原列国掀起轩然大波:蛮夷岂能模仿?赵雍亲往反对派领袖公子成府上劝说,力陈宽袍大袖、笨重战车的拙劣,终于克服重重阻力,改革军服、改革战法。接下来的11年,赵国四战四胜灭掉心腹之患中山国,驯服林胡、楼烦两大蛮族,成为战国后期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2300多年前胡服骑射这一历史典故,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历史启迪:一支军队的变革助推着一个国家的振兴。
近代以来尤其如此。反观鸦片战争以后百年间的中国,无论是“剑”不如人、“剑法”不如人,还是“剑气”不如人,总之是军力不如人,军队观念陈旧、体制僵化、老气横秋。即便改革,也是修修补补、三心二意、局部而不彻底,拖累得国家任人宰割、人民任人欺凌。
斗转星移。如今,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关口,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机遇、大挑战。国际力量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体系加速演变、深刻调整,几个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却未改变,我国安全环境更加复杂,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道路崎岖不平。就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人民军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进行着浴火重生的变革重塑。
什么是时代?这就是时代。什么是使命?这就是使命。重大的使命无一不来自伟大时代的召唤,军队的改革与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
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群体、哪个职业像军人这样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军人始终是使命感最强的一群人。他们的眼里有国家、有民族,也有危机、有忧患,还有敌人、有战斗。正因此,人们看到,每当重大改革来临的时候,一声令下,三军齐动,自上而下,雷厉风行。
1985年百万大裁军开始之际,军委领导找时任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谈话,征询合并整编后的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人选,谢振华秉公推荐他人。军委领导又征询谢振华是否愿意去另一个大单位工作。从当时情况看,很快将恢复军衔制,留任大军区正职的开国将军,应会被授上将军衔。谢振华对此非常清楚,但他表态:“我愿意把位子让给较年轻的同志,对我的工作就不要再考虑了。我愿回去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昆明军区最后一段光荣的历史使命。”9月1日,“昆明军区善后办公室”正式挂牌。在谢振华的带领下,善后工作圆满完成,而他也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
今天,从将军到士兵,这样的故事仍在延续。在真正的军人看来,与肩负的重大使命相比,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舍弃?
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这张照片,再次凝视这根手指,它立起的是一个标准,指明的是一个方向。这个象征性的“一”,是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一”,是听从号令万众一心的“一”。如果非要用数字来标定它的分量,那应该是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