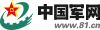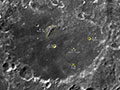用速度杀伤的“极速杀手”
正是看到了动能拦截武器作为未来战场“极速杀手”的可能,目前世界各军事强国竞相投入相关武器系统研究,主要着力于拦截弹道导弹和攻击在轨卫星,力图将动能拦截武器打造成构建反导系统和反卫星系统的“战场铁拳”。
如在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中,“爱国者-3”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地基拦截弹、海基“标准-3”拦截弹、NCADE空基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和NFIRE天基拦截器等,都是典型的动能拦截武器。“爱国者-3”是美国陆军所采用的低空防御系统,主要采用改进型增程拦截弹进行撞击毁伤。可用于陆基机动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也采用了动能拦截器对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进行末段拦截。相比之下,“爱国者-3”拦截弹主要对末段低空飞行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萨德”反导系统的动能拦截弹重点对付末段高空飞行的弹道导弹。

俄罗斯S-500反导系统
而作为俄罗斯最新研制的防空导弹系统,“S-500”反导系统中的77N6N1导弹也可以选择动能碰撞杀伤拦截器,专门用于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外大气层高超音速飞行器等高速飞行的目标。当然,迄今为止,试验拦截成功率最高的仍属美军研制的海基中段反导系统,其动能拦截弹理论上可对初段、中段和末段飞行的弹道导弹进行有效拦截。
为维持在太空中的军事优势,美、俄等军事强国同样将动能拦截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太空。美军从1989年就开始重点发展“机载动能反卫星武器”和“陆基动能反卫星武器”等动能拦截反卫星武器。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研制拦截高度800至1000千米的动能拦截反卫星弹。1997年8月,由美国陆军研制的“动能杀伤拦截器”样机进行了首次悬浮飞行试验,并在悬浮过程中保持对目标的精确定位攻击。到2008年2月,美国海军从“宙斯盾”战舰、“伊利湖”号巡洋舰上发射了改进型“标准-3”导弹,在太平洋上空准确击毁了距地面247千米高空运行的间谍侦察卫星USA-193,“秀”出了其动能拦截反卫星的实战能力。
在“以动制动”中不断发展
动能拦截武器的出现,带动了各种防御和攻击系统进入非核时代,不仅可用于弹道导弹的防御,还可用于空天反卫星作战、反飞机渗透作战等。未来甚至可专门用于反炮弹作战,是一体化作战的“多面手”,势必成为未来战场打击方式的主流。
然而,战场上“硬碰硬”的较量,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躲避拦截,正在研制中的下一代弹道导弹,将能在末端实施机动飞行或同时释放多个诱饵,在空中形成一个由弹头、弹体、诱饵组成的“战场谜团”,使得反导系统无法找准真正的目标。为此,动能拦截也需要升级“以多对多”的“分身术”。
目前,有的军事强国已启动微型拦截器技术计划,正在研发蜂群拦截器、微型拦截器和多杀伤拦截器等多种微型动能拦截器,只需一枚拦截弹就能携带数以百计的微型拦截器。研制出的小型低成本拦截器,采用1公斤重的微型拦截器,通过子母弹方式一次发射大量微型拦截器,能实现战区范围内50至400米对作战车辆和固定目标的区域防御。
除向小型化、微型化方向发展外,动能拦截还将立足针对未来战争威胁,进一步克服现有结构复杂、成本过高等短板,努力提升智能化水平。目前,一些军事强国十分重视对新型动能拦截器的研究探索,如有的国家海军和陆军联合推出毫米波导引头技术倡议计划,着力为动能拦截器配上“火眼金睛”。有关机构正在计划研制和试验传感器硬件方案、智能处理和传感器数据融合算法,力图实现动能拦截的智能处理。
未来,动能拦截的战场应用还有诸多可能。如美国陆军研制的“瞄准线反坦克武器系统”,安装在改装后的“悍马”M1113战车上,其最大射程已超过了美军车载“陶”式反坦克导弹。其另一款“紧凑动能导弹”是新一代超高速动能反坦克导弹,其超高的动能和内置的钨制穿甲弹头具备了穿透所有装甲系统的能力,同时还具有打击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能力,可广泛应用于装甲坦克战、野外堡垒战等。
供图: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