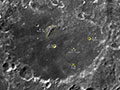忠实记录时代精彩
■朱金平
报告文学,是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写作体裁。
报告文学以记录时代、反映现实为己任,题材广泛。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包身工》,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再到迎接改革开放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后来的军旅报告文学《蓝军司令》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报告文学有短篇、中篇、长篇之分:一般2万字以下的为短篇,2万至10万字之间的为中篇,10万字以上的为长篇。就内容而言,报告文学又可分为事件类、人物类、工作类等。但不管什么样内容的报告文学,都有其写作规律可循。
在长时间的记者生涯中,我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进行了一些探索。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我简单谈谈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些认识。
——突出一个主题。这是一篇报告文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大报告文学有大主题,小报告文学有小主题。这个主题,必须正确、鲜明、独特。如果作者的立场不对,其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很可能就是错误的;如果主题含糊、云里雾里,读者就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如果主题与其他作品过于雷同,又会给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乏味感。主题确定下来后,才能够围绕这个灵魂组织材料,决定哪些内容应该作为重点详写、哪些内容可以一笔带过,以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语言风格。例如,曾有位战士在公共汽车上帮助一位大妈抓小偷却因此带来一系列曲折经历。在确定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时,经过深入思考,我就将其主题定为“今生无悔”,希望通过这件事传达给社会一种“见义勇为不图回报”的正能量。
——讲述精彩故事。新闻要讲故事,文学要讲故事,报告文学当然也必须讲故事。故事不精彩,对受众就没有吸引力。那种泛泛而谈的叙述或无病呻吟的抒情,是报告文学写作的大忌。故事从哪里来?当然要靠扎实细致地采访。生活中的许多故事,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精彩,靠作者坐在斗室里闭门造车是想不出来的。只要采访的功夫到家了,不愁找不到故事。故事多了,还有个选择的功夫。采访时要以十当一,写作时要以一当十。著名战地记者、作家魏巍在朝鲜战场上撰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时,面对着采访到的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素材,最后只选择了3个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故事,这也使其成为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有了故事,还有一个怎么讲的问题,这就要在结构上动脑筋。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撰写的报告文学《一个超极限生命的追问》,采取倒叙结构,把读者带入到紧张的地震救援现场。
——注重细节描述。许多人看过一部精彩的影视剧或小说,多年之后,连作品名称可能都忘记了,却仍然能清楚记得其中的某个生动细节。这就是细节的魅力!细节,是故事叙述的最小单元,却最能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事物的本质。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尤其是人物类报告文学和事件类报告文学中,细节的描写尤为重要。即使宏大叙事,也不可忽视细节的作用。那些生动的细节从哪里来?还是要靠作者深入、细致、扎实地采访。2017年4月,我去新疆塔斯提边防连采访班长王克怀,挖掘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那1岁多的儿子随母亲来队期间,只要早上一听到连队起床的哨音,就会像爸爸一样蹦下床,光着一双小脚跟着爸爸出操,妈妈再拉也不行。于是,连队出操的队伍后面,就跟着一个“小尾巴”,嘴里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这个小细节折射出戍边官兵后继有人的主题。于是,我把这个细节写进了报告文学《一棵小白杨》中。作品最先被《人民日报》刊发,后来在被作为福建中考作文分析试题和上海出版社的语文阅读范文时,这个细节都被保留下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内容完全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许有的人认为,凡文学作品都可虚构,这是一种误解。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具有新闻属性,是客观事物的真实记录,不能有任何虚构的成分。作品中的“5个W”必须齐全,缺一不可。除人名、时间、地点这些“硬件”必须完全真实之外,对事情经过、因果关系及人物心理之类的“软件”,也必须客观真实地加以叙述。任何细节,都不能编造。文学要有想象力,但这种想象力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是用来还原事实的,不是用来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的。曾经有个报告文学作者,为了一个典型人物事迹的生动,编造了许多“感人”的情节,结果作品发表出来后,不仅受到读者质疑,也被报道中的主人公批评。这个教训值得汲取。即使有些事实非常过硬,但由于给人缺乏真实感,作品里也应慎用。
——语言鲜活生动。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外衣,同样也是报告文学的外衣。一篇报告文学要让读者喜爱,不能不讲究语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学”。古人有“语不惊人死不休”及“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追求,今人应该在文学语言上有更高的要求。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不论描写什么事物,我们必须不断地苦心思索,非发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不可。类似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思索困难,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我们国家的语言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报告文学作者应在继承我国语言养分的基础之上,努力吸收时代最精彩的语句。巴尔扎克说:“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蠢材。” 文学语言,贵在创新。尤其是报告文学,打着时代的烙印,语言也必然要与时代合拍。语言新颖、生动、流畅,读起来才会让人如饮甘醴。
——注入澎湃激情。一个歌唱演员如果缺乏激情,演唱时让人直打瞌睡,那谁还愿意看他的演出?为什么许多人喜欢看足球等体育比赛?因为那能点燃观众心中的激情。同样,报告文学作品要能够打动人,作者胸中必须澎湃着生命的激情。如此,他才能笔下飞流三千尺,指间卷起万堆雪,使作品产生感人肺腑的力量。作者的激情哪里来?来自对祖国、对党、对军队、对人民深沉的爱恋,来自灵魂深处的正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我为那些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关键时刻向着疫区勇敢逆行的医务工作者们而感动,为那些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全力参与抗疫的人民子弟兵、公安干警、各级干部群众的奉献精神而赞叹,为那些在病毒的袭击下不幸遇难的鲜活生命而感伤。那些天,泪水常常模糊了我的双眼。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让中国告诉世界、让今天启示未来。所以,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我终于完成了4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武汉保卫战》,受到了读者朋友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