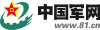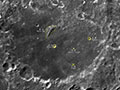三、日军并非首次对我使用“黄弹”
“黄弹”指装填糜烂性毒剂芥子气、路易氏气或二者混合的炮弹。芥子气(日本称之为黄剂1号)于1917年7月由德军首次使用。其纯品是没有臭味的无色油状液体,工业品因含杂质呈黄色、棕色至深褐色,有较浓的芥末或大蒜的味道,能够很快渗透纺织品、皮革、纸板、薄橡皮等。路易氏剂(黄剂2号)纯品也是没有臭味的无色油状液体,工业品为棕褐色,有天竺葵气味,渗透性比芥子气强,对橡胶等防毒材料也有很强的渗透性。糜烂性毒剂曾一度被称作毒气之王,是典型的持久性毒剂,防护处置十分复杂。
日军大本营于1937年7月27日下达“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催泪筒”命令后,于1938年4月就使用呕吐性毒剂(红剂)做出指示,命令各部队在复杂的山区作战时可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使用呕吐性毒剂,并要求尽量与烟幕弹同时使用。1939年5月13日,日军参谋总长下达的“大陆指”第452号明确指示,“华北方面军可在现占领地域的作战中使用黄剂等特种资材,以研究其在作战中的价值。”但要“采取完全措施,隐藏使用的事实,特别要严防对第三国人员造成伤害,并对其严格保密。尽量减少对中国军队以外的普通外国人的伤害。实施限于山西省内便于保密之偏僻地区,并仅限于达到试验研究之目的。”这一指示,为日军在山西使用糜烂性毒剂开了绿灯;文中特别将外国人摈除,是害怕在国际社会暴露罪行及遭到拥有更强化武能力的美英等国家对等报复。
日军的“黄弹”共有6种,分别为:野山炮用弹、105榴加用尖头弹、150榴用尖头弹、92式空投弹、94式轻迫击炮用弹、100式50千克炸弹。其中,迫击第5大队装备的是94式轻迫击炮用弹,于1935年实现制式化。日军《对交付上海派遣军毒气器材的意见》表明,1937年11月期间,要求“单就运送炮弹而言,以后不用再运送黄弹”。因而,可以推测当时日军已经配备了大量黄弹。其将“黄弹”运进华北的时间早于1938年3月。据《关于转送特种黄弹件》《关于特种弹运送件》资料记述,1938年3月上旬兵站总监多田骏中将申请,将168吨“特种弹L1号(黄剂1号)”和23.8吨“特种弹L2号(黄剂2号)”运往内地,10895发“黄A(轻型迫击炮弹药筒)”、2762发“黄E”等大量黄弹运往东北和华北。
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发现的日军第5迫击大队战斗详报,评价针对首次使用“黄弹” ,“效果非常好”。他认为,日军知道毒气战违反国际法,可能是判断在山西的山区里使用毒剂不会被外界发现,所以将之选为首次使用糜烂性毒剂的区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日军早就在中国进行了“黄弹”的试验与实战使用。
1928年7月,日军便在台湾新竹进行了糜烂性毒剂芥子气的热带试验。
1937年11月进攻南京时,日军计划大量使用“黄弹”。日军第10军《关于进攻南京的意见 》提及的第一方案是“急袭”,第二方案是先迅速包围南京,然后用“芥子气弹、燃烧弹等对南京进行彻底的连续一周的轰炸,使南京成为废墟。”理由之一是,“在该攻坚战中,彻底使用毒气极为重要,不能容忍像上海战役那样,对使用毒气犹豫不决,从而付出重大牺牲。”
1938年5月11日,5名医师一致认定日军在台儿庄作战中使用了芥子气,“中毒士兵两眼红肿、失明,身体出现溃烂性溃疡。”
1938年7月中旬,山西闻喜。闻喜、曲沃、垣曲之役,敌军以久疲之师,遭我军主力部队包围歼击,屡战屡败,于羞恼之余,乃不顾公法人道,于7月中旬使用极剧烈之糜烂性及催泪性瓦斯向我军发射(1938年7月22日《新华日报》)。
1938年5月3日,八路军第129师先先遣纵队在徐家X战斗遭到日军毒气袭击,中毒人员有部分发生皮肤病,状态是发展后皮上起水泡,泡破即流黄水,流一处烂一处,泡主要在面上和脚上(1939年5月3日先纵关于如何医治中毒人员致129师电)。
1938年7月,山西垣曲。7月,垣曲之役敌损失甚多,遂恼羞成怒,向我军施放催泪性及糜烂性毒气。我军虽有准备,但中毒者仍甚多(1938年7月27日《抗敌报》)。
1939年3月中旬,山西。据兴集电:此次晋西作战我军受炮伤者呈苍白色,创部浮肿,四周生绿色水泡,刺破后流黄绿色浓水,据判断为中毒所致(1939年3月19日《新华日报》)。
1938年9月10日,湖北广济。当我第26军于9月10日重新控制公路及松阳桥时,日军为了挽救败局,竟连续三次对松阳桥及其东南高地发射装有芥子气、路易氏气混合毒气的炮弹,造成第26军大量人员中毒和地面染毒而使反攻受挫。当日,当第44师卫生队赴现场抢救,行至全扣湾时,先行人员即有中毒者,附近的水牛也已倒在地上。当晚派往的侦察人员行至五里墩、十里铺附近,即已中毒抬回(《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729页,1938年9月13日李品仙致蒋介石电))。
1938年9月25日,湖北当阳。由瑞昌以西向木石港进犯之敌继续增兵攻势更猛,并施放窒息性、糜烂性毒气,我军颇有伤亡(1938年9月28日《新华日报》)。
1938年11月3日,河北阜平。此次阜平作战,我中毒部队有一团大部,三团一个营,七一七团四个连。中毒后即刺激眼流泪、鼻喷嚏,头昏或脸发红,发肿,呼吸不畅,全身无力,胀肚子。轻者用冷水洗后,须四天才能恢复原状。最重者红肿特甚,过两天后复在红肿处起泡,如同火烧状,但不甚痛,除用冷水洗外,用日光皂与冷开水用毛巾擦泡处,即消去,好时要脱一层皮(聂荣臻关于阜平作战敌施放毒气及我防毒经验的通报)。
可见,至少在1938年9月,日军已经知道将芥子气、路易氏混合使用。因为普通芥子气(黄1号)容易结晶,与路易氏气混合使用效果更好,适合寒冷地区。从“华北方面军”于1939年5月13日接到大本营下达的“大陆指”第452号关于试用黄剂的命令开始,日军大量使用黄弹,为以后的使用积累经验。日军对第36师团从1940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在华北进行春季晋南作战的经验总结中写道:“暂时性和持久性毒气混合使用效果甚佳,在精神上也能取得相当大的效果。”
此外,日军在《武汉作战期间化学战实施报告》中提及化学战教训:“迫击大队需要编制汽车与驮马。目前虽有辎重车辆编制,但毋庸赘言,其装置量和机动性不理想。凡辎重车可以通过的地形,通常货运汽车也可通过,且迫击炮重量轻,易于手工搬运,故可编制汽车,只有在复杂地形实施作战时才需编制驮马。”关于“红剂”的精神效果,“使用初期,其精神相当大,但待敌军认识到红剂的实际效力后,其作用逐渐降低……红剂作为所谓奇袭兵器的价值已经下降。”可以说,武汉会战中,日军第5迫击大队通过大量使用毒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对毒性更强、更难防护的“黄弹”有了进一步需求。
四、日军毒气战文件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研究
化学武器因其大规模杀伤性,成为国际公法明文禁止使用的战争手段。日本侵略者背弃《日内瓦议定书》,野蛮使用化学武器屠杀中国军民,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所能堕落的最底线。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立即将化学武器的使用作为重要的战略部署。
由于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掩盖化学战真相,从始至终,对化学武器的研究、生产、试验、部署、使用以及相关文件资料等都按机密程序运作。从参谋总长指示到化学战部队战斗详报,都有要求做好毒气战保密工作的内容。其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使用化学武器采取不承认主义,秘密使用并极力销毁罪证。战争结束之际,则将没来得及用完的化学武器进行掩埋、倾入江河,文件资料则予以销毁。尔后,还专门下达文件,指示在毒气战上统一口径。部分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方面的战犯和文件资料则被利欲熏心的美国人运回国内,用于推动其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计划。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也有不少化学战的密件。只有少数化学战文件资料散落在民间。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侵华日军为避免留下战争犯罪证据而废弃了记录类文件,该战斗详报可能是由部队相关人士私人保管而被留存下来。此次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发现的战斗详报就是流落民间的化学战资料。可以推测,随着更多的国外资料解密和民间资料被发现,还会有更多的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将公之于世。
如果今后能够有重点地搜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各迫击大队、野战毒气厂、毒气中队、毒气小队的战斗详报,以及收集整理日军各迫击大队发展史和回忆史料,将会有更多的毒气战例出现。尽管日军化学战的罪证姗姗来迟,但更多的真相终将得到揭示!
(作者曾为防化专业军官,现为军事科学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