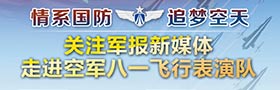战友讲述:他就是龙思泉无疑
战友是谁?战友是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亦是亲历者,已过世。
苍翠环抱的陵园,有一座坟墓,墓前矗立着高大的石碑,碑上刻着三个大字“红军坟”。碑前的左侧有一尊铜像,是一位短发的红军女卫生员,她左手抱着一个婴儿,右手拿着汤匙给婴儿喂药。铜像的脚背被前来瞻仰的人摩得光滑发亮。铜像前长方形的香炉中,香灰堆积,插着许多燃烧着的香,烟雾缭绕。
1965年夏天,贵州遵义凤凰山麓,湘水之滨,我第一次见到当地口口相传的“红军菩萨”。
这座坟是1935年3月由遵义桑木桠的人民群众在当地建造的,当时就立有一块刻有“红军坟”字样的石碑。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时,将“红军坟”由桑木桠迁入“红军烈士陵园”。至此,来“红军坟”瞻仰、祭奠、扫墓的人络绎不绝。
“红军坟”中的烈士是谁?站在铜像前,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个疑问。因为,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撤离遵义,我团奉命进驻,是最后撤离遵义的部队。我当时任团里的军医。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团没有女军医、女卫生员,甚至全师都没有女的。
尘封的记忆一点点开启。
“龙思泉呢?”撤离遵义、一渡赤水后,我寻找着常常在一块探讨“共产主义与土豆炖牛肉”的战友,那个十八岁的卫生员。
“龙思泉失踪了。”二营的人告诉我。
原来,部队在遵义出发前,有一位农民苦苦哀求龙思泉去二十里外他的家里,给他病得很严重的父亲治病。龙思泉平时为周围的群众送医送药,细致、耐心,又有家传的中医中药知识,疗效较好,名声渐大,所以这位农民才远道来请。经领导批准后,龙思泉随农民而去,至第二天部队撤离他还没有归队,以后也没有跟上来。二营的领导一致认为:“龙思泉是一位优秀卫生员。他不会开小差,这么久没有归队,被敌人杀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个“红军坟”埋葬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女红军,还是我的战友龙思泉?
当时时间有限,无法细究,以后又由于工作繁忙未及查证。直到我退休后,才开始多方调查了解,并在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协助下,深入当地群众中做了细致的调查考证,终于使“红军坟”得以见“庐山真面目”。
我们找到了当年参加埋葬这位红军遗体的两位农民,证明这位红军是男的,而不是女的。而埋葬红军遗体的带头人就是二营营部驻地的房东,他指出这位红军就是住在他家的红军卫生员。由此可以确认,这位红军,就是为农民治病后下落不明的二营卫生员龙思泉无疑。
1929年,龙思泉在家乡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当了红军。由于他懂得一些医伤治病的技术,参军不久就在连队当了卫生员。后来调营部工作,担任营卫生员。1933年,龙思泉所在的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称号,龙思泉也受到团的表扬,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当时他身上一直背着的红十字药箱,也是从广西带过来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