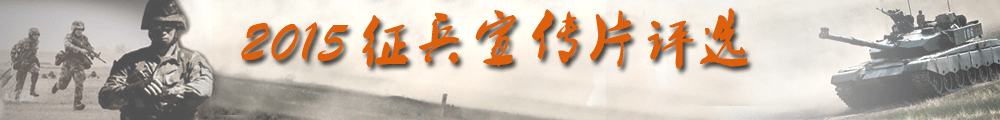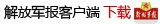三、令美军咋舌的“中航效率”
日军攻占缅甸时,在那里的英军、印度军和中国远征军乱成一团,彼此都失去了联系。空中紧急救援,成了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空运部队的首要任务。
l942年5月的一天,中国航空公司著名飞行员陈文宽正在执行从重庆到加尔各答的航班,飞机上乘坐着6名乘客。飞行途中突然报告说有日本战斗机出现,陈文宽立即紧急着陆,机组人员与乘客全躲在离飞机不远的一条壕沟里。过一会,警报解除,飞机又开始飞行。由于油不够,飞机在密支那着陆加油。机场此时一片混乱,许多人趁加油时爬上了飞机,只能容纳21人的客舱一下子挤得满满的,陈文宽一点:好家伙!共72人。谁也不愿下飞机,因为日军已攻到城南,并向机场奔来。没有办法,陈文宽只好还未等加完油就强行起飞。天黑了,飞机歪歪扭扭降落在加尔各答机场,这时突然又从行李舱里冒出了6名旅客。
老飞行员周炳笑着讲起了这个故事。他告诉记者,1944年他一到中航参加驼峰空运,就听许多同事讲过这个故事。
中国的航空人员就是这样在战火中锻炼成长。在英军从仰光大撤退时,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命令美军两架飞机从印度向缅甸急运一批物资,尤其在加尔各答的200吨药品前线更为急需。结果,美军只空运了12吨货物,而中航公司一下运了72吨。中国的运输机成了印缅战场上的空运主力,运送了大量弹药、汽油,还撤退了2400多人。一位美国顾问在向罗斯福报告中说,在卡拉奇有1300吨主要物资,在阿萨姆有700吨,都等待运输。要完成运输工作,“我倒希望由泛美和中国航空公司处理整个事情”。
据有关资料,1942年7月,美军的20架飞机只运了73吨物资去中国,而中航公司的10架飞机却运了1293吨物资。这一悬殊差距使美国最高决策机构有意想把整个驼蜂空运的任务交给中航公司来负责。
史迪威将军对美军的表现虽不满意,但这位个性很强的老头却坚待要求在战区里必须由军方负责空运,中航公司只能签合同来接受任务。然而,史迪威也一时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民营公司的效率在战争中会远远超过训练有素的美军空运部队?
记者在采访中对此也很感兴趣。潘国定和陆元斌老人说道:中航公司的管理很有效率,另外飞机每班都是超负荷运输,而且一干一天就是10来个小时。飞行人员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多是比较优秀的飞行员。外籍飞行员比中国飞行员的收入要高一倍,但中国飞行员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拼命地干。记者问:“多干是否会增加收入?”老人回答说:“多干当然收入会多,但大家不仅仅是为了钱在汀江,大家住的都是很简陋的平房,上了飞机后没吃没喝,一干就是一整天。许多飞行员来自沦陷区,大家多么希望能早日驱逐日寇、回到可爱的故乡。飞行员中有许多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他们参加空运,也是为了祖国能早日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在整个驼峰空运中,虽然,中航公司的货运量只占整个空运货运量的11%,但其效率始终高于美军空运部队好几倍。
抗战救亡是所有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这一心声汇成了一股巨大力量,是会超出常规的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放射出来。
周炳老人告诉记者: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中航公司的飞行员,战后都成了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一些到了国外的飞行员,也都成了这些国家民航公司的主力。
四、一条不成文规定
驼峰航线充满了危险与艰难。在这条航线上,一架又一架飞机消失了,一批又一批飞行人员一去不复返了。1946年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刊文描述驼峰空运时说:“……至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而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堆作为航行的地标”。杨宏量老人告诉记者:“直至今天,当飞机在这些地域上空飞过,还能看见当年飞机的残骸。”
陆元斌老人回忆说:“驼峰空运的最后一个航班也没有闯过鬼门关。那是1945年11月,一架飞机从汀江运器材到四川泸州,在返程时刚起飞不久就摔了。”
驼峰航线的危险性使美国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凡是在这条航线上飞行的美籍人员可以免服军役。
危险来自多方面。
处于中缅印交界处的密支那被日军攻占后,密支那成了日军空军基地。密支那距汀江只有250英里,而日本零式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为450英里,他们要袭扰汀江、昆明和中途拦截驼峰空运飞机轻而易举。
在驼峰航线上飞了500多次的潘国定回忆道:“我们空运是东西向飞,日机是南北线打我们。有一次,我瞧见日本战斗机追来了,赶紧超低飞行。日机从我上面飞过,直追着前一架美军飞机打,我看着美机被打得稀烂。”陆元斌老人说:“由于我们经常夜航,日寇战斗机也就经常在夜里出动拦截。有一个晚上,美军一下损失了13架,中国航空公司丢失了两架。”
除了被日机击落的一部分之外,大部分失事飞机是缘于复杂的地形与恶劣的气候条件。
从汀江到昆明,以及后来开辟的从汀江到叙府(今四川宜宾)、从汀江到泸州的驼峰航线上,到处是崇山峻岭,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高黎贡山、玉龙雪山等20多座高山,大多海拔在四五千米以上,山岭连绵起伏,峰顶耸立云霄。许多地区渺无人烟,人若落入深山野林之中,几乎难以生还。
对飞行来说,更糟的还有恶劣的天气。从5月中旬开始,驼峰航线上有5个月是雨季。倾盆大雨常常使飞机油箱内的雨水凝聚,造成飞机停车。大风,是驼峰航线又一大天敌。冬天的大风猛烈得能使飞机偏离航线甚至被吹得无影无踪。飞行中还经常会碰上强烈的雷暴和剧烈的气流冲击,这股气流能使飞机在1分钟内上下颠簸幅度达几千英尺。春秋季节经常出现方向不定的怪风,更使飞机屡遭不测。
陆元斌老人谈到,1944年3月,中航公司一位叫黄官悦的飞行员驾机从汀江夜航昆明,因顺风太大,飞机上的自动定向仪失效,飞行员不知自己飞到了哪里。机智的黄官悦便把飞机的一台发动机关掉,用另一发动机以最小油门保持飞行高度,在空中盘旋,一直等到天亮后,才发现自己早已飞过了昆明。
周炳在1945年的春季也遇到了一次险情。当时飞机正往汀江赶,老天突然翻脸,狂风暴雨袭来,飞机被迫绕了一个圈子,结果油耗尽,滑翔了一阵后,最后只能在离汀江不远的地方迫降。
日机的拦截、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气候,再加上飞机性能差、沿途缺乏导航和备降机场,一旦出事,生还希望很小。虽然飞行员都备有降落伞,但跳伞落入崇山峻岭之中,要想活着走出来十分困难。1943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组织缅甸克钦族人成立救护队,营救美军空运队空中跳伞的飞行员,结果全年只营救了125人,这个数字不到全部坠机人数的三分之一。剩余的人有的死于森林之中,有的被日军俘虏,有的尸体长期悬挂在树上被蚂蚁啃掉。
死亡威胁着每一个飞行员。谁都知道随时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但谁也没有把死放在心上。周炳、杨宏量两位老人谈到:也许是由于战争磨炼了人们的意志,大家对死都想得很坦然,每次出发时没有人会提心吊胆地走,也不会满口豪言壮语、怀着悲壮的心情走出宿舍,总是带着平静的心境登机出发,归来时也不会欢天喜地庆贺自己幸运。经常有伙伴出发后再也没有回来,也经常有新伙伴补充上来。大家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日夜飞行在驼峰线上,坚持到抗战胜利。但说对死一点不怕也是假的。在伙伴中间就有一条不成文规定:“不能找人替飞”。派到你去飞,正巧碰上你生病或有急事要办,你不能找人替你去飞,而应该向公司请假,由公司另派人。否则,一旦找人替飞遇难,不但遇难者成了替死鬼,而且你自己的良心也会受到谴责而抱憾终身。